老僧辨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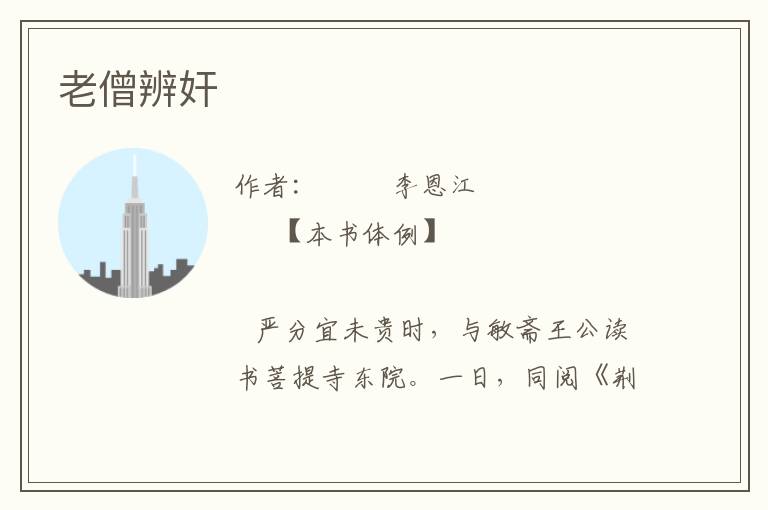
作者: 李恩江 【本書體例】
嚴分宜未貴時,與敏齋王公讀書菩提寺東院。一日,同閱《荊軻傳》,至樊于期自殺處,嚴曰:“此騃漢也!事知濟不濟,輒以頭顱作兒戲耶?”遂大笑。王曰:“烈士復仇,殺身不顧,志可哀也!”遂大哭。又閱至白衣冠送別時,嚴復大笑曰:“既知一去不還,乃復遣之使去,太子丹真下愚也!”王又大哭曰:“壯士一行,風蕭水咽,擊筑高歌,千古尚有余痛。”繼閱至提劍斫,箕踞高罵,嚴更笑不可仰,曰:“是真不更事漢!不于環柱時殺之,而乃以嫚罵了事。”王更涕泗沾襟曰:“豪杰上報知已,至死尚有生氣。銅柱一中,祖龍亦應膽落。”一時哭聲笑聲,喧雜滿堂。一老僧傾聽久之,嘆曰:“哭者人情,笑者真不可測也!二十年后,忠臣義士無遺類矣!”
后王官中牟縣令,頗有政聲。而嚴竟以青詞作相,專權誤國,植黨傾良,為明代奸邪之冠。老僧預知之,而不能救,殆佛門所謂定劫歟!
鐸曰:“傳言愚忠愚孝,有旨哉!古之亂臣賊子,皆聰明絕頂人也。是故,士不重才而重德。”
(選自《諧鐸》)
嚴嵩入仕之前,曾經同王敏齋一起在一所佛寺的東跨院讀書。有一天,一同閱讀《史記·刺客列傳》中的荊軻傳部分,讀到樊于期自殺的地方,嚴嵩說:“這是個呆漢!知道事情不能成功,還拿腦袋當兒戲呀?”就大笑起來。王敏齋說:“義烈之士為了報仇,連殺身都不顧惜,其志氣真讓人敬重并為這痛惜!”就大哭起來。又讀到燕國的太子丹等人穿著白衣裳、戴著白帽子為荊軻送別的時候,嚴嵩又大笑,說:“既然知道有去無回,準定失敗,卻又遣送荊軻,叫他前往,太子丹真是個下等的愚人!”王敏齋又大哭,說:“壯士一去,風為之蕭蕭而鳴,易水為之鳴咽而泣,高漸離擊筑,大家高唱悲壯的惜別之歌,此情此景,千年之后讀來還令人悲痛。”接著讀到荊軻刺秦王不中,秦王的侍醫夏無且用所帶的藥囊擲荊軻,秦王拔出寶劍,把荊軻砍成重傷,荊軻坐在地上,兩腿侮辱性前伸呈簸箕形,破口大罵,這時嚴嵩更是笑彎了腰,說:“這人真是個沒有辦事經驗的莽漢!不在秦王繞著柱子逃跑的時候殺掉他,卻竟然用嫚罵了事。”王敏齋更是哭得厲害,眼淚鼻涕沾滿衣襟,說:“英雄豪杰報答知己的尊長,英氣勃發,雖然連受重傷,可是一直到死都堅貞不屈,呼呼有生氣。荊軻的匕首一下擲中了銅柱,秦王也應是嚇破了膽。”一時間哭聲、笑聲,交織在一起,滿堂喧嘩成一片。一位老僧傾耳細聽了好久,嘆息道:“哭的人是發自正常人的至情,笑的人全無人性,真是居心叵測!玩弄政治是此等人之長,二十年后,忠臣義士恐怕要遭其陷害,一個也剩不下了!”后來王敏齋作官作到中牟縣令,政績很好,很有名譽。而嚴嵩竟然從進獻祭天的青詞入仕起作到宰相,專權誤國,拉攏黨羽傾陷忠良,成了明朝最大的奸臣。老僧預先知道這些,可是不能事先挽救,這大概就是佛家所謂的一定的劫數吧!
鐸詞:“社會上流傳的格言稱愚鈍的人才能當忠臣、作孝子,大有深意呀!古代的亂臣賊子,都是絕頂聰明的人。因此,對于讀書人來說,最重要的不是才而是德。”
筆記小說,來源于平民百姓的街談巷語、道聽途說,文人筆之于書的時候,又予以加工潤色,所以,它與文人自作之小說有所不同,具有記錄奇聞遺事的性質,篇幅大多短小,刻劃人物不要求面面俱到,敘述情節也大多繁簡隨意,并不要求首尾完具。然而,雖然是一鱗半爪,吉光片羽,卻往往以其形象的鮮明、生動、典型、吸引人們的注意,它是我國文學園地中一叢別有風致的花朵。
本文不足四百字,只記了嚴嵩和王敏齋入仕之先同在菩提寺東跨院讀書時同讀荊軻傳的一段情事。此事芥豆之微、平凡無奇,然而作者卻寫得詞采紛呈:嚴嵩之笑、王敏齋之哭、老僧之嘆,宛然耳畔,以小見大,刻劃了嚴嵩不講道義、機心自用,急功近利的齷齪性格。嚴氏三笑,一笑樊于期,不知事情濟不濟,先以頭顱作兒戲;二笑太子丹、既知事情難成,仍復遣荊軻使去;三笑荊軻,不于環柱時殺掉秦王,終以嫚罵了事。當然,三個人的作法,樊于期之輕生、太子丹之不待條件成熟而遣荊軻、荊軻之欲生劫秦王,都不無可議,但他不表示同情,而極盡嘲笑之能事,卻是全無心肝者。三位都是忠臣孝子、英雄豪杰,嚴嵩好象全然不懂;也可能道不同不相為謀,每遇好人就本能地反感。王氏三哭,形成鮮明的對比,從相反的角度襯托嚴氏的性格。一哭樊于期自殺,為報“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之仇,不惜性命,義無反顧;二哭太子丹之送荊軻,明知敵我不敵,仍然大義凜然,作玉碎之搏;三哭荊軻刺秦王不中,烈士殉身,豪氣干云。他完全被書中英雄人物的英雄事跡所感動。哭笑同時,且強度一次比一次增加,又一絲不亂,確是絕妙章法。老僧之嘆,不為無見,但斷定二十年后忠臣義士因之無遺類卻是江湖術士的口吻,以一時一事斷人平生是靠不住的,只能說彼此有聯系有影響。然而,嚴嵩確為明代奸邪之冠,史有明文。作者據其讀書時的一件小事,以文學虛構的方式,燭照從前,一似豐富了他的生平。后人創作大部頭嚴嵩傳,可做為很好的素材。正象老僧之預言失之主觀片面,作者文末的結語也不免武斷荒謬,忠孝是政治、倫理的概念,聰愚是對人智力條件的評價,二者并無必然聯系。人生一世,德是至關重要的,但要提倡德才兼備;不然,滑到無才便是德的極端,世事就不堪問了。
作者文筆老辣,語言精煉而不失活潑,善于通過對話表現人物性格,本篇也體現這種特色。但說到此篇寫作特點,我們以為是行文的簡括。三哭和三笑的原因,沒有一份《史記》的《刺客列傳》在側,是無法徹底弄懂的。這種寫法恐怕只在筆記小說中有,象老朋友談心,都知道的就從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