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山二首·顧炎武》原文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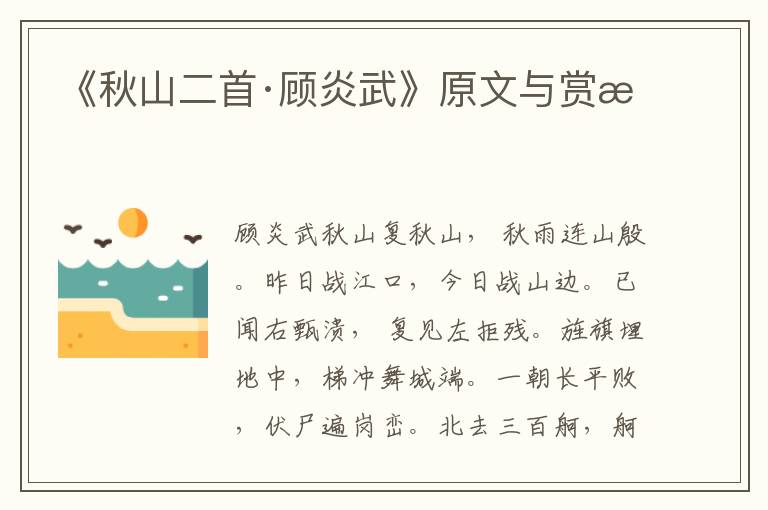
顧炎武
秋山復秋山, 秋雨連山殷。昨日戰江口,今日戰山邊。已聞右甄潰, 復見左拒殘。旌旗埋地中,梯沖舞城端。一朝長平敗,伏尸遍崗巒。北去三百舸,舸舸好紅顏。吳口擁橐駝, 鳴笳入燕關。昔時鄢郢人, 猶在城南間。
秋山復秋水, 秋花紅未已。秋風吹山岡, 磷火來城市。天狗下巫門, 白虹屬軍壘。可憐壯哉縣, 一旦生荊杞。 歸元賢大夫, 斷脰良家子。楚人固焚麇, 庶幾歆舊祀。勾踐棲山中, 國人能致死。嘆息思古人,存亡自今始。
顧炎武(1613—1681),字寧人,昆山縣亭林鎮人,世尊稱為亭林先生。幼孤,于書無所不讀,明末參加南京鄉試時,加入復社。清兵南侵,屢起抗清。最后定居于陜西華陰,墾田度地,讀書如常。他學問淵博,著作極多,負盛名的有《天下郡國利病書》、《日知錄》、《唐韻正》等十多種。寫詩追求質實深厚,樸素沉郁,繼承杜甫的現實主義傳統,多沈雄悲壯之作。論詩以言志為本、觀民風為用,提倡“詩主性情,不貴奇巧”。對當時的詩壇產生積極影響。
這兩首詩寫于順治二年(1645),反映了江南大屠殺的情況。這年五月清兵陷南京,七月占領蘇州、昆山。江陰、嘉定、松江等地人民奮起反抗,遭到滿清貴族的屠殺與鎮壓,極其慘烈。詩篇描述當時清軍進軍之快,歌頌人民的壯烈斗爭事跡,表達自己義不臣虜的心愿。
第一首寫江南人民的反抗及清軍燒殺搶掠。“秋山復秋山,秋雨連山殷”。秋山連著秋山,綿綿秋雨把江南的山石淋得鮮紅,這比喻江南抗清斗爭一浪連著一浪,人民前仆后繼,鮮血淋漓,高度概括了彼時的史實。嘉定人民曾三次舉義旗抗清, 皆不幸失敗,遭屠戮。史稱“嘉定三屠”。嘉定人民參加斗爭的前后共十八萬人,犧牲了兩萬多人。后來江陰人民又進行不屈的斗爭,但終因援盡糧絕,城破。城內男女老幼無一投降。清軍大屠三天,殺十七萬二千多人,未死老小只五十三人,城內血沒足脛。清軍死傷也很慘重,被擊斃三王十八將及士卒七萬五千多人。(韓菼(江陰城守記》)當時抗清起義風起云涌,僅在江南就還有金聲、吳應箕、江天一為首的徽州起義,沈猶龍、陳子龍、夏允彝為首的松江起義,吳易、孫兆奎為首的太湖起義,朱集璜、王佐才、陳大任為首的昆山起義,屠象美領導的嘉興反剃發起義以及顧炎武本人、歸莊為首的蘇州起義……古人常把“秋雨”叫做苦雨。所以說此詩頭兩句內容含量極大,歌頌了江南人民在凄風苦雨中的英勇斗爭,揭露滿清貴族屠刀過處血流成河的罪行,戰斗力很強。“昨日”以下六句為具體描寫,閏六月初一江陰起事,典史陳明遇主兵,徽人邵康公為將,兩人守本城,以明朝都司周瑞龍率部泊江口,成犄角之勢。“昨日戰江口”,指周部跟清軍在江邊激戰失利,清軍逼城下。“今日戰山邊”,江陰城在君山山邊。“已聞右甄潰,復見左拒殘。”右甄,右翼的長陣;左拒, 左翼的方陣。《明史·閻應元傳》:“康公戰不勝,瑞龍水軍亦敗去。明遇乃請應元入城,屬以兵事。……劉良佐用牛皮帳攻城東北。……八月廿一日大清兵從祥符寺后門入。”“旌旗埋地中,梯沖舞城端。”據徐嘉說,此補嘉定之戰的情況。作者自注:“《漢書·李陵傳》: ‘于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七月初四日五更,大雨如注, 嘉定城上兵民露天戰斗三晝夜,兩眼腫爛,遍身淋濕,飲食斷絕。領隊的侯峒曾、黃淳耀等也仗劍挺立雨中。堅守兩月余的軍民已疲憊不堪,難以支撐。清軍用大炮轟城,墻垣坍塌,接著用云梯登城, 以沖車上缺口,擁進城內。“一朝長平敗,伏尸遍崗巒。”嘉定城中無一投降,上自薦紳, 下至百姓, 幾乎全部殉難。長平敗,以戰國故事暗喻清軍屠城之殘酷。長平,趙國邑名,故城在今山西高平縣西北。秦昭襄王十七年,秦將白起大敗趙兵于長平,活埋趙卒四十萬人。以上寫清軍進軍迅速和義軍不幸失敗。“北去”以下四句寫清軍奸淫燒殺的暴行。“北去三百舸,舸舸好紅顏。”《嘉定屠城紀略》:“婦女寢陋者, 一見輒殺;大家閨秀及民間婦女有美色者皆生擄。白晝宣淫。不從者釘其兩手于板,乃逼淫之。嘉定風俗雅重婦節,慘死無數。”僅漢奸李成棟(原為明朝徐州總兵)一人就用了三百只大船才運走了他所擄掠的子女玉帛、牛羊馬豕。“吳口擁橐駝,鳴笳入燕關。”吳口,作者自注:“《晉書·慕容超載記》: ‘使送吳口千人。’”即吳地子女。橐駝,駱駝。鳴笳,吹胡笳。燕關,燕地的關塞,滿族基地在白山黑水間,清國盛京在沈陽。四句說,向北駛去的無數大船,船上都是美女,連岸上行走的駱駝背上、車上也裝滿了。滿清貴族得意洋洋地吹著胡笳,將搶到的吳地人財運往北方老窩。真是欲哭無淚的一幅亡國后的悲慘圖景!“昔時鄢郢人,猶在城南間。”鄢郢,作者自注:“《戰國策》:雍門司馬謂齊王曰,鄢陵之大夫不欲為秦(降服于秦),而在城南下者以百數。”意思是,國土雖被清兵占領,但是不愿投降的人還很多。這是贊揚在淫威下不屈的志士,他們是民族的脊梁。
第二首寫戰爭給城鄉帶來蕭索荒涼,贊頌江南人民的斗爭意志。“秋山復秋水,秋花紅未已。”仍用寫景來象征血跡未干,余慟彌深,反抗愈烈。“秋風吹山岡,磷火來城市。天狗下巫門, 白虹屬軍壘。”徐嘉解說,寫蘇州失陷事。秋風蕭殺,鬼火入城,給人帶來災禍。天狗星落在蘇州城的巫門上,兇險的兵象——白色的虹連綴著一座又一座軍營。敵人殺氣騰騰,蘇州橫遭蹂躪。詩人將清軍比著“磷火”、“天狗”、“白虹”,表現鮮明的憎恨。“可憐壯哉縣,一旦生荊杞。”江陰、嘉定、昆山、蘇州等府縣原都是全國首富之區,經劫掠后,荊棘遍地,成了廢墟。壯哉縣,出《史記·陳平世家》,指富庶大縣,沃野無際。這兩句深深嘆息,抒發國破家亡的哀怨。“歸元賢大夫,斷脰良家子。”在入侵的魔爪下,萬眾一心,合力作戰。賢大夫即清官士子, 良家子即好百姓,他們都英勇捐軀,血灑戰場,拋頭顱,獻生命。歸元,斷頭;斷脰,斷頸。這兩句概括漢族兒女所作的艱苦卓絕、可歌可泣的抗爭。“楚人”四句以歷史故事委婉地贊揚江南人民抗清的決心。“楚人固焚麇,庶幾歆舊祀。”作者自注:“《左傳》定(公)五年:吳師居麇(今湖南省岳陽市東南),(楚)子期將焚之(以火還擊吳軍)。子西曰: ‘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 ‘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又戰。”楚國終于打敗了吳軍。歆舊祀,享用累年來的祭品。“勾踐棲山中,國人能致死。”據《國語》,越王勾踐棲會稽山中,臥薪嘗膽,最后使越國人上下齊心,敢出死力,終于滅吳報仇。這四句說,當年楚人堅決火攻入侵麇地的吳軍,父兄的遺體橫陳沙場也顧不得了,為了祖國火燒吳軍,父兄遺體也被燒掉,就讓忠魂安享以往的祭品。越王勾踐不忘亡國恥辱,終于依靠人民力量滅吳復國。以此勸勉江南人民不要因暫時的曲折而氣餒,應該繼承父兄遺志,學習勾踐精神,作長期奮斗的準備。再用“嘆息思古人,存亡自今始”結束全詩,再次強調存亡繼絕,自今開始,大有希望,應當踏踏實實地干下去。
《秋山二首》是顧炎武詩歌的代表作,歷來備受贊譽。他深切體會到民族壓迫的痛苦,詩中洋溢著亡國之痛, 顯示出不屈不撓永遠進擊的意志,燃燒著愛國熱情,充滿抗清必勝的信念。由于作者是當時學術界執牛耳者,所以《秋山》、《千里》等詩寫成后,即不脛而走,在復社成員中產生巨大影響,鼓勵遺民詩人堅持操守,寫出大量充溢正氣的戰斗樂章。藝術上,《秋山》繼承了杜甫的現實主義精神,反映當前戰斗的生活,抒發深切的情感體驗,從而形成激楚蒼涼、深沉蘊含的風格。沈德潛說:“寧人肆力于學……窮極根柢,韻語其余事也。然詞必己出,事必精當,風霜之氣,松柏之質,兩者兼有。就詩品論,亦不肯作第二流人。”(《明詩別裁集》)彭紹升說:“至于國家存亡之際,慷慨傷懷,或揚聲哀號,或幽憂飲泣,以視屈原、賈生諸公時遇不同,同一天性激發而已矣。”(《亭林先生余集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