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怨·劉方平》原文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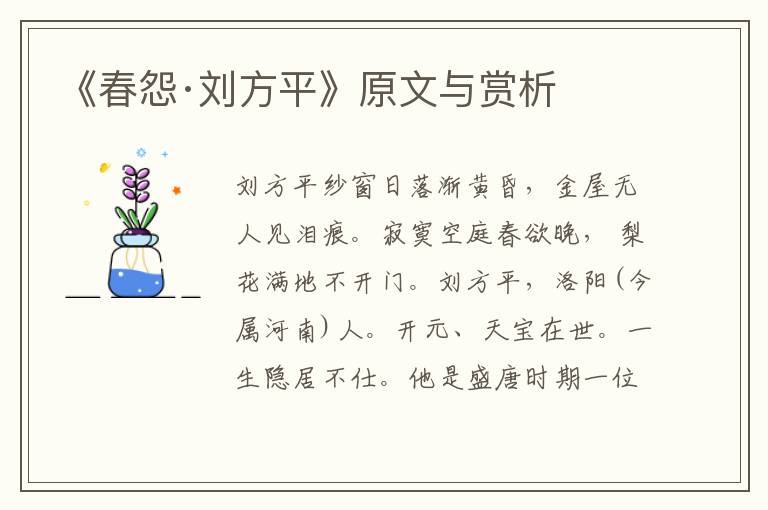
劉方平
紗窗日落漸黃昏,金屋無人見淚痕。
寂寞空庭春欲晚, 梨花滿地不開門。
劉方平,洛陽(今屬河南)人。開元、天寶在世。一生隱居不仕。他是盛唐時期一位不很出名的詩人,存詩不多。但留下的幾首小詩卻寫得獨具一格,頗有功力。詩多詠物寫景之作,尤擅絕句。
一首詩如同一首樂曲,必須要有調(diào)子。列寧說過:“沒有調(diào)子算什么詩呢?它們達不到人的心靈”(轉(zhuǎn)引自1961年1月21日《文匯報》)。所謂調(diào)子,是指作品的內(nèi)在聲音,即灌注于作品中的能夠觸動讀者心弦,引起共鳴的感情。這關(guān)系到藝術(shù)感染力的問題。詩貴情,情貴真,沒有真情,哪有詩意,也就不可能走進讀者的心靈。劉方平的《春怨》,寫得言言深切,字字沉痛,情噴滿紙,確是動人肺腑的。
詩人從怨春的角度來寫宮怨,哀婉凄絕。起句“紗窗日落漸黃昏”,就給人以夕陽西下,夜幕將垂的精神重壓。“紗窗”,把入目的視野,縮小到室內(nèi),能使人預(yù)感到在這里有什么文章要做了。“漸”,有時間在過去的動覺,似乎天色越來越暗。緊接著, 一讀第二句“金屋無人見淚痕”,讓我們看到了一位以淚洗面的宮人。“金屋”,用漢武帝初寵陳皇后(小名阿嬌)的典故。漢武帝小時,姑母抱置膝上,問:“兒欲得婦否?”漢武帝指著姑母的女兒說:“若得阿嬌,當(dāng)以金屋貯之。”陳皇后后被棄長門,過著幽禁的凄涼生活。“金屋”,住這里是冷宮的借代。失寵的宮人,沒有了寵幸之盛,沒有了宴歌之娛,她囚居孤室,無人作伴,傷心落淚卻沒誰看見, 也就是說,連同情憐憫她的人也找不到。“淚”而有“痕”,暗指哭的時日久了,她陷入在天地長久有時盡,此怨綿綿無絕期的萬分悲痛之中。室內(nèi)沉寂得象與世隔絕似的,那室外又是怎樣呢?第三句“寂寞空庭春欲晚”,是第二句意思的鋪延,是說整個的庭院空蕩蕩地不見一個人影,沒有一點兒活氣,加上是暮春季節(jié),沒有綻開的繁花,沒有生命的歡樂,這是什么地方啊!“春欲晚”的“欲”字下得好,說明春將消逝,包含著宮人有怨春歸去的愁悵之情。她挽不住春天移動的腳步,嘆恨不已。人們總是把春季比作人的青少年時代。“眾芳蕪穢,美人遲暮”,她會由花事已盡,想到自己年華的流逝,這就為她的淚水之所以無語傾瀉, 乃至久而留痕,提供了具體的心理印證。結(jié)句“梨花滿地不開門”,進一步襯托了失寵宮人的怨春情緒。已不是春風(fēng)一吹,“千樹萬樹梨花開”的時節(jié)了。辭春的梨花,四散飄零,遍地皆是,這會引起種種的惱人情懷。詩人將人物的感情與自然景象聯(lián)系起來,意興蕭索,透露了生活在這樣的環(huán)境里的宮人纏回的凄苦。
全詩色調(diào)灰冷,富有象征意蘊,以“日落”推出“黃昏”,以“春欲晚”示現(xiàn)“梨花遍地”,作為女主人公身世命運的形象寫照,使景情化, 又使情景化,遞邅交迭而不見跡象,頗為難得。另外,“淚痕”的“無人見”,庭空門掩,應(yīng)合了女主人公的心境,寫盡了她的衷曲與酸楚,象彈琴有弦外之音, 如吃橄欖有回甘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