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有度第六》譯文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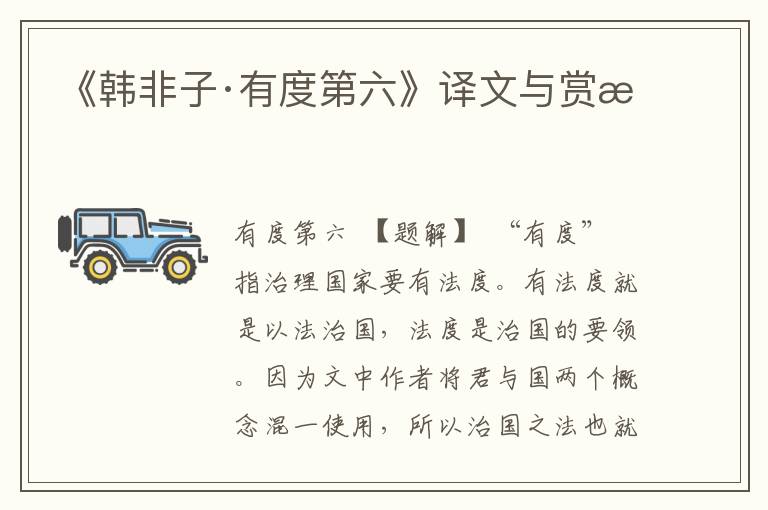
有度第六
【題解】
“有度”指治理國家要有法度。有法度就是以法治國,法度是治國的要領(lǐng)。因為文中作者將君與國兩個概念混一使用,所以治國之法也就成了君王的權(quán)術(shù),或者反過來說君王私下的權(quán)術(shù)等于治理國家的法令。韓非從他所吸取的歷史經(jīng)驗教訓(xùn)中認(rèn)識到國家有法即君王有術(shù)的重要性,于是,他徹底否定了儒家廉、忠、仁、義等道德范疇,倡導(dǎo)臣民都專一于君王的意志;他又從道家無為學(xué)說中得到啟示,認(rèn)為君王只要“因法數(shù)”即“任勢”就能實現(xiàn)“獨制”、“獨斷”、“上尊而不侵”的目的。至此,其法、術(shù)、勢學(xué)說的全部思想都統(tǒng)一到“尊君”這一主旨上了。
【原文】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荊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氓社稷[1]也,而荊以亡。齊桓公并國三十,啟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2]。燕襄王以河為境,以薊為國,襲涿、方城,殘齊,平中山,有燕者重,無燕者輕;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趙救燕,取地河?xùn)|;攻盡陶、魏之地;加兵于齊,私平陸之都;攻韓拔管,勝于淇下;睢陽之事,荊軍老而走;蔡、召陵之事,荊軍破;兵四布于天下,威行于冠帶之國;安釐死而魏以亡。故有荊莊、齊桓公,則荊、齊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則燕、魏可以強[3]。今皆亡國者,其群臣官吏皆務(wù)所以亂而不務(wù)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則是負(fù)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
【注釋】
[1]荊莊王:即楚莊王,春秋時期五霸之一。氓:古代稱外來的百姓為氓,這里用為百姓之意。社稷:土神和谷神,古代君主都祭祀社稷,后來就用社稷代表國家。[2]齊桓公:春秋時齊國國君,姓姜,名小白。公元前685年-643年在位。春秋時期著名的五霸之一。啟:打開。[3]燕襄王:即燕昭王,戰(zhàn)國時期燕國君主。薊:(jì)古地名。燕國的都城。在今北京城西南部。魏安釐王:名圉,戰(zhàn)國時期魏國君主。
【譯文】
國家沒有長久的強、也沒有長久的弱。執(zhí)法者強國家就強,執(zhí)法者弱國家就弱。楚莊王吞并了二十六個國家,開拓了三千里疆土,莊王的百姓組成國家后,而楚國也就衰弱了。齊桓公吞并了三十個國家,擴展了三千里領(lǐng)土,桓公的百姓組成國家后,齊國也就滅亡了。燕襄王以黃河為國境,以薊為國都,侵襲涿州、方城,攻占了齊國的部分領(lǐng)土,平定了中山國,于是,擁護燕人的國家就受到重視,不擁護燕人的國家就受到輕視;襄王的百姓組成國家后,燕國也就滅亡了。魏安釐王攻打趙國救助燕國,奪取了黃河以東的土地,又攻打定陶、衛(wèi)國之地;又對齊國發(fā)兵,把平陸占為己有,攻打韓國占領(lǐng)管地,在淇水邊大獲全勝;在睢陽發(fā)生的魏、楚戰(zhàn)事中,楚軍疲憊而撤退;在上蔡和召陵戰(zhàn)爭中,楚軍被擊敗;魏兵遍布天下,在講究禮儀和禮教的國家顯示威風(fēng);安釐王去世,魏國就滅亡了。所以有了楚莊王、齊桓公,那么楚國、齊國就可以稱霸;有了燕襄王、魏安釐王,那么燕國、魏國就可以強大。這些國家如今都亡國了,就是因為群臣官吏專干混亂的勾當(dāng)而不去做治理國家的事。他們的國家衰弱了,他們又不顧國法營私舞弊,這實在是背著干柴去滅火,國家的混亂衰弱就越嚴(yán)重了。
【原文】
故當(dāng)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偽;審得失有權(quán)衡之稱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若以黨舉官,則民務(wù)交而不求用于法[1]。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術(shù),比周以相為也。忘主外交,以進其與,則其下所以為上者薄矣。交眾、與多,外內(nèi)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故忠臣危死于非罪,奸邪之臣安利于無功。忠臣之所以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奸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奸臣進矣。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群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法矣。數(shù)至能人之門,不壹至主之廷;百利私家之便,不壹圖主之國。屬數(shù)雖多,非所尊君也;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托于群臣之家也。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wù)相益,不務(wù)厚國;大臣務(wù)相尊,而不務(wù)尊君;小臣奉祿養(yǎng)交,不以官為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斷于法,而信下為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弊,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故主讎法則可也[2]。
【注釋】
[1]比周:結(jié)黨營私。[2]弊:通“蔽”。遮蓋、遮擋之意。讎:這里用為“用”之意。
【譯文】
所以在當(dāng)今這個時代,能去除私利而追求公道法則的國家,百姓安定而國家得到治理;能去除私利而推行公道法則的國家,就會兵強而使敵人衰弱。所以審查得失有法度依靠的君主能凌駕在群臣之上,那么君主就不可能被臣下用狡詐虛偽的手段欺騙;審查得失有權(quán)衡考慮的君主聽取遠方的事情,那么君主就不可能被臣下用天下的輕重來欺騙了。現(xiàn)在如果根據(jù)聲譽來提拔人才,那么臣下就會背離君主而在下面緊密勾結(jié);如果以朋黨關(guān)系來推舉官吏,那么臣下就會致力于勾結(jié)拉攏而不根據(jù)法度求得任用。所以官吏們沒有能力國家就會混亂。以贊譽來獎賞,以毀滅來懲罰,那么喜好獎賞厭惡懲罰的人,就會拋棄公正的法度,玩弄陰謀手段,結(jié)黨營私互相吹捧。他們不顧君主的利益在外私交,培植他們的黨羽,那么臣下為君主著想和盡力的地方也就少了。交結(jié)廣泛、黨羽眾多,在朝廷內(nèi)外結(jié)成朋黨,雖然他們犯了大錯,但為他們掩藏罪責(zé)的人也多。所以忠臣在無罪的情況下也遭受危難與死亡,而奸臣卻在無功的情況下依然得利。忠臣之所以遭受到危難與死亡的原因并不是因為有罪,那么賢良的臣子就會潛伏退隱了;奸邪的臣子得到利益并不是因為有功勞,那么奸臣就會得到提拔。這就是滅亡的根本。像這樣下去,群臣就會摒棄法治而重視私利、輕視國法了。他們屢次奔走奸臣門下,一次也不去君主朝廷;想方設(shè)法謀私利,一點也不為國家大事著想。屬臣數(shù)目雖不少,不能用來侍奉君主;百官雖具備,不能用來承擔(dān)國事。這樣,君主就徒有虛名,而實際上是依附于群臣的。所以我說:衰弱國家的朝廷沒有可用的人。朝廷里邊沒有人,不是指朝廷衰弱了,而是指臣下竭力互謀私利,不竭力利國;大臣竭力互相推崇,不竭力尊奉君主;小臣拿俸祿私下交結(jié),不把官職放在心上。導(dǎo)致這種情況的原因,是由于君主在上不依法斷事,而聽?wèi){臣下任意去干。所以明君用法選人,不用己意推舉;用法定功,不用己意測度。能干的人不可能埋沒,敗事的人不可能掩飾,徒有聲譽的人不可能升官,僅受非議的人不可能辭退,那么君主對臣下就辨得清楚而易于管理了,所以君主依法辦事就可以了。
【原文】
賢者之為人臣,北面委質(zhì),無有二心;朝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順上之為,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1]。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而上盡制之。為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脩頭,下以脩足;輕暖寒熱,不得不救入;鏌铘傅體,不敢弗搏[2]。無私賢哲之臣,無私事能之士。故民不越鄉(xiāng)而交,無百里之慼[3]。貴賤不相逾,愚智提衡而立,治之至也。今夫輕爵祿,易去亡,以擇其主,臣不謂廉。詐說逆法,倍主強諫,臣不謂忠[4]。行惠施利,收下為名,臣不謂仁。離俗隱居,而以作非上,臣不謂義。外使諸侯,內(nèi)耗其國,伺其危險之陂,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毀國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謂智。此數(shù)物者,險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所簡也[5]。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無或作惡,從王之路[6]。”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廢私術(shù),專意一行,具以待任。
【注釋】
[1]質(zhì):抵押品或人質(zhì)。[2]鏌铘:古代利劍名。傅:靠近、迫近。[3]慼:(qī)通“戚”。這里用為親戚之意。[4]倍:后作“背”。背棄,背叛之意。[5]陂:邊際、旁邊。簡:通“諫”。這里用為諫諍,直言規(guī)勸之意。[6]或:通“惑”。這里用為迷惑之意。路:道路,引申為行動的途徑,這里指法度。
【譯文】
賢能的人做臣子,面朝北把自己交給君主,沒有二心;在朝廷上不敢推辭低賤之事,在軍旅中不敢推辭艱難之事;順從上級的領(lǐng)導(dǎo),服從君主的法令,摒除自己的成見來等待上級命令而不作是非判斷。所以他有口而不講私事,有眼而不看私情,而完全接受上級管理。做臣子的,如同雙手,上用來理頭,下用來理腳;冷暖寒暑,不能不管;刀劍近身,不敢不拼。不因私偏袒賢明臣子,不因私寵愛智能之士。所以百姓不離鄉(xiāng)私交,沒有百里之外的親戚。貴賤不逾越,愚智平等地生存,這是治國的最高境界。當(dāng)今那種輕視爵祿,輕易流亡,去選擇其他的主子的,我不認(rèn)為是廉。謊言抗法,違背君主而強行進諫,我不認(rèn)為是忠。施行恩惠,收買人心來抬高自己的聲望,我不認(rèn)為是仁。避世隱居,而用謊言非議君主,我不認(rèn)為是義。出使他國,損害祖國,眼睜睜看著祖國陷入危境,便恐嚇君主說:“外交沒有我就不能友好,外患沒有我就不能解除。”而君主也便相信他,把國家托付給他;這樣,貶低君主名聲來抬高自己,損害國家利益來便利私家,我不認(rèn)為是智。這幾種行為,是亂世君主喜歡的,先王法度反對的。先王法度是這樣說的:“臣下不要沉迷于作威作福,不要沉迷于利益,要聽從君王的指揮;不迷惑于作惡,要順從君王的道路。”古代太平盛世的百姓,實行公正之法,丟棄私利手段,忠心跟從君王,全部候命待任。
【原文】
夫為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且上用目,則下飾觀;上用耳,則下飾聲;上用慮,則下繁辭。先王以三者為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數(shù)、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內(nèi),聰智不得用其詐,險躁不得關(guān)其佞,奸邪無所依[1]。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朝廷群下,直湊單微,不敢相逾越[2]。故治不足而日有余,上之任勢使然也。
【注釋】
[1]要:古同“約”。這里用為約言之意。以明誓的方式就某事作出莊嚴(yán)的承諾或表示某種決心。亦指所訂立的誓約、盟約。關(guān):(ɡuān)通“貫”。這里用為貫通、貫穿之意。佞:(nìnɡ)這里用為花言巧語之意。[2]郎中:(lánɡ)郎,古廊字。原指宮殿廷廊,置侍衛(wèi)人員所在。官名。戰(zhàn)國始置。帝王侍從官侍郎、中郎、郎中等的通稱。其職責(zé)原為護衛(wèi)陪從、隨時建議,備顧問差遣等侍從之職。郎官一直沿用到清朝。如:郎官(郎中及員外郎的泛稱);郎中(郎官。漢代稱中郎、侍郎、郎中為郎官,掌星宿之職);郎將(官名);郎署(宿衛(wèi)官的官署)。
【譯文】
做君主的親自考察百官,就會時間不夠,精力不足。而且君主用眼睛看,臣子就修飾外表;君主用耳朵聽,臣子就修飾言辭;君主用腦子想,臣子就夸夸其談。先王認(rèn)為這三種器官不夠,所以不依賴自己的才能而依賴法術(shù),嚴(yán)明賞罰。先王依照盟約做,所以法律簡單而且誰都不敢去侵犯,所以能獨自管理天下,再聰明的人也不能欺騙別人,再陰險暴躁的人也不能貫通他們的花言巧語,奸邪之人就沒有依靠了。即使遠在千里之外,也不敢改變話語;即使有郎中官的權(quán)勢,也不敢隱藏好事而掩飾壞人;朝廷的群臣百官,都聚集微薄的力量獻給君主,不敢互相超越職守。所以君主要處理的事用不了一天時間而且還有空閑,這就是君主運用權(quán)勢的結(jié)果。
【原文】
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漸以往,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1]于法之外,不為惠于法之內(nèi),動無非法。法,所以凌過游外私也;嚴(yán)刑,所以遂令懲下也[2]。威不貳錯,制不共門[3]。威、制共,則眾邪彰矣;法不信,則君行危矣;刑不斷,則邪不能勝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guī)矩為度;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為比,故繩直而枉木斫,準(zhǔn)夷而高科削,權(quán)衡縣而重益輕,斗石設(shè)而多益少[4]。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法不阿貴,繩不撓曲[5]。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絀羨齊非,一民之軌,莫如法[6]。屬官威民,退淫殆,止詐偽,莫如刑[7]。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法審,則上尊而不侵[8]。上尊而不侵,則主強而守要,故先王貴之而傳之[9]。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
【注釋】
[1]游:放縱。[2]凌:假借為“夌”。本意為侵犯,這里用為打擊之意。[3]威不貳錯:威勢不能兩方面共同樹立。貳,指君臣兩方面。錯通“措”。置,引申為樹立。[4]夷:本意為平和、平易,這里用為平準(zhǔn)之意。科:通“窠”。坎、坑之意。縣:古通“懸”。這里用為懸掛、倒懸之意。[5]阿:曲從、迎合。[6]繆:(miù)通“樛”。絞結(jié)之意。絀:(chū)通“黜”。這里用為貶退之意。羨:貪慕之意。齊:同等,相等之意。[7]屬:連接。威:這里用為“法則”之意。淫:過度。殆:假借為“怠”。懶惰。[8]易:這里用為輕視之意。含有“不以為意”的意思。[9]貴:崇尚、重視。
【譯文】
為人臣子侵害他的君主,就像地形起伏一樣,逐漸地變化下去,就會使君主迷失方向,東西方位調(diào)了頭而自己還不知道。所以先王設(shè)置司南之官來端正清晨和傍晚的方向。所以明智的君主使群臣百官不在法律之外打主意,也不在法律之內(nèi)亂施恩惠,一舉一動沒有不合法的。法,是用來打擊違法和游于法律之外的私行的;嚴(yán)刑,是貫徹法令、懲罰下屬的。威勢不能君臣兩方面同時樹立,權(quán)力不能君臣共同擁有。威勢與權(quán)力如果君臣共同擁有,那么眾多的邪者就肆無忌憚了;執(zhí)法不講信用,那么君主的行為就危險了;刑罰不果斷,那么就戰(zhàn)勝不了邪惡的勢力。所以說,巧匠心目中認(rèn)為符合墨繩,還是要先以規(guī)矩為度量;有上等智慧的人辦事,還是先要以先王的方法為根據(jù),所以墨線拉直了斜木材就可以斬直,水平儀放平了凸凹不平的木材就可以削平,秤懸掛起來就可以去重就輕使之平衡,斗與石設(shè)置起來就可以減多益少使之平均。所以以法治國,就是為了約束人們的行為。法令不袒護權(quán)貴,墨繩不屈從彎木。法令該制裁的,即使智者行為也不能躲避,勇者也不敢抵抗?fàn)庌q。懲處過失不回避大臣,獎賞善行不漏掉百姓。所以矯正上級的過失,追究下級的不正之風(fēng),治理混亂,解決謬誤,貶退貪慕,平定是非,統(tǒng)一民眾的規(guī)范,沒有比得上法律的。整治官吏,威懾民眾,摒棄淫亂怠惰,制止狡詐虛偽,沒有比得上刑罰的。刑罰重了,百官就不敢因高貴而輕視卑微的;法制審明,君主尊貴不受侵害。君主尊貴不受侵害,君主就強勁而遵守約定。所以先王重法并把它傳下來。君主丟棄法而用私,上下級之間就沒有差別了。
【評析】
有度,就是有法度。韓非通過舉例說明,誰掌握住法度,誰就能強大。韓非把“依法治理”看得很高,認(rèn)為只有以法治國,用法來規(guī)范人們的社會行為,國家才能變得強盛。
同時,在選拔任用人才的問題上也需要運用一定的法度。依據(jù)法度來衡量人才,才能真正做到公平。公平地選拔任用人才,才能使各級官員各司其職,忠心報國。選用賢臣也是有標(biāo)準(zhǔn)的。韓非認(rèn)為,賢臣的標(biāo)準(zhǔn)就是忠心不二地服務(wù)君主,當(dāng)好君主的得力助手。
韓非在文章的第四段提及了誠信問題,誰是賢臣?誰是佞臣?的確很難辨別!所以古代君王就運用盟約、誓約的方法,好的就賞賜,壞的就處罰。所以,領(lǐng)導(dǎo)人不必去操心誰是賢臣,誰是佞臣,誰是小人,只要能干事,就是能臣。這就是現(xiàn)代所說的量才使用。
文章的最后一節(jié)則轉(zhuǎn)而談到凡事要有準(zhǔn)則。要以法辦事,依法辦事,要以法治國,依法治國。以法律為準(zhǔn)繩,以法律為規(guī)矩,才能把事情處理妥當(dāng)。本段提出的“法不阿貴”的思想被視為古代法治思想史上的精髓,是對戰(zhàn)國之前“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貴族法權(quán)的否定,具有進步的歷史意義。“矯上之失”、“一民之軌”,更具有平等的法制觀念,它是“法不阿貴”思想的進一步發(fā)展,體現(xiàn)了依法治國的思想,他排除了“釋法用私”的人治行為,不準(zhǔn)許用法以外的個人意志管理政事,不準(zhǔn)許用私心實施賞罰,這些思想在中國法治思想史上具有開創(chuàng)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