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瓦希里詩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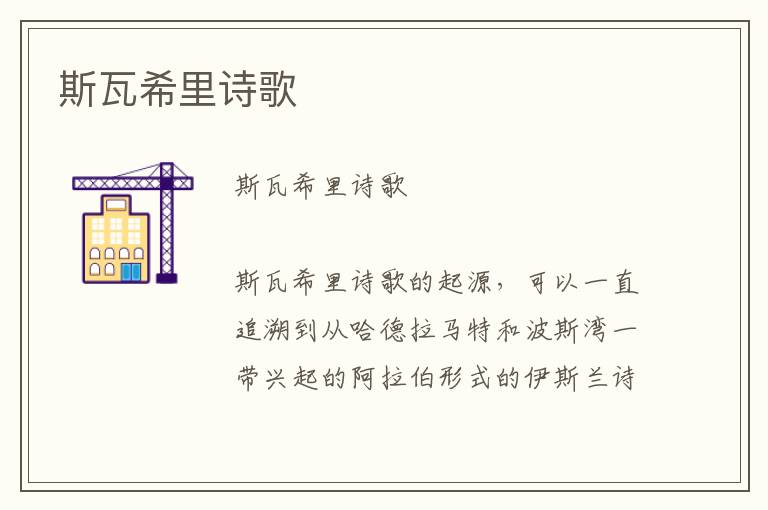
斯瓦希里詩歌
斯瓦希里詩歌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從哈德拉馬特和波斯灣一帶興起的阿拉伯形式的伊斯蘭詩歌。19世紀斯瓦希里詩歌的發展,顯示了這種從外國傳入的形式在東非沿海地區社會的影響下已非洲化。現存最早的斯瓦希里詩稿作于18世紀初。其中一首《阿爾—哈姆齊亞》有460節,以斯瓦希里語再現了阿拉伯詩《萬村之母》。另一首《泰布卡之詩》有1150節,描寫了公元628至636年阿拉伯與拜占廷之間的戰爭。現在的斯瓦希里詩歌,有一部分仍然用經過修改的阿拉伯字體書寫,但僅在傳統的穆斯林—斯瓦希里社會中流傳。在書籍或報刊雜志上發表的斯瓦希里詩歌則都是用羅馬字母書寫的。
斯瓦希里詩歌最重要的詩律特點,是它的押韻以及音律單元的固定形式。現存最早的婚禮歌曲、小夜曲以及頌歌的詩行都很長,音節數多少不確定,但至少有15個音節。大英博物館里保存的一首詩作(展品第4534號),則是早期斯瓦希里詩歌的另一種形式,稱作“塔克米斯體”。它的每一節都有5行,韻腳是aaaab,沒有行中停頓;這首是賽義德·阿卜杜拉·賓·納西爾酋長(1725—1820)所作,描寫富莫·李昂戈的傳奇故事。阿卜·巴克爾·賓·薩利姆酋長(卒于1584)的后裔哈德拉米·賽義德家族,曾對斯瓦希里詩歌作出過重要的貢獻。《阿爾—哈姆齊亞》的作者是阿卜·巴克爾酋長的曾孫賽義德·艾達魯斯。賽義德·阿卜杜拉·賓·納西爾酋長也寫過一首十分流行的“烏坦迪體”詩《自省》,描寫了東非沿海城邦衰落的情形。賽義德·曼薩布酋長則擅長寫離合體詩與說教詩。
“烏坦迪體”每節由4個半行組成,其中前3個半行韻腳相同,第4個半行尾韻作為每一節的最后韻腳而不斷重復。這種詩歌形式用于寫口頭詩歌傳統的長篇敘事詩,例如:關于李昂戈這類英雄的傳奇故事,以及關于歷史和當代事件的重要記錄,例如1905年的馬及—馬及起義以及現代肯尼亞和坦桑尼亞人為爭取獨立而進行的戰爭。一些篇幅較長的“坦迪”詩是從阿拉伯敘事詩衍生出來的。這些詩歌稱作“襲擊文學”,由一些傳奇故事構成,取材于先知穆罕默德于公元622年從麥加逃到麥地那以后歷次戰爭的歷史事實。有些較短的“坦迪體”詩往往溯源于阿拉伯文學,描寫先知的降生和早期生活。
斯瓦希里詩中,抒情詩或主題詩最流行的形式每節含8個半行,每個半行由8個音節組成,其韻式為abababbc;每節最后的韻腳在全詩中重復出現。盡管這種形式在書寫中作為單行或雙行來使用,但學者們一般仍稱之為四行體。這種詩體在斯瓦希里詩歌中還沒有一個公認的名稱。無論從形式還是題材方面來講,它都不同于“烏坦迪體”或“塔克米斯體”;它的音節數可以有所變化,但基本是固定的。斯瓦希里四行體的杰出倡導者,是蒙巴薩的穆亞卡·賓·哈吉·阿爾—賈桑尼(1776—1840)。穆亞卡發展了斯瓦希里詩歌。他用詩歌表達人們對現實事件的態度,從而大大地推進了斯瓦希里詩歌的世俗化。
現代斯瓦希里詩歌的四行體多用于表現世俗題材,但這些詩歌的思想傾向往往比較保守。在斯瓦希里語成為坦桑尼亞國語之后,羅伯特·夏巴尼(1776—1840)成為一位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要作家。是他率先擴大了斯瓦希里語在民族文學創作中的使用范圍,是他首先使用斯瓦希里語借用英國隨筆、中篇小說、自傳等體裁進行創作。他的詩作富于傳統色彩而深受歡迎。
另一位重要的當代詩人是馬蒂亞斯·姆尼亞姆帕拉(1919—1969)。1968年,尼雷爾總統曾邀請一批坦桑尼亞詩人座談,希望他們能運用自己的才智向農民宣傳民族政治。姆尼亞姆帕拉就是被接見的詩人之一。他始創了“恩貢杰拉”(即對口詩),將斯瓦希里詩歌搬上舞臺,這種表演旨在教育民眾,提倡“良好行為、本土文化以及民族政治”。這種使詩歌為民族服務的創作方向,繼承了斯瓦希里詩歌主導的社會功能。但在東非沿海地區的斯瓦希里音樂俱樂部里所演唱的詩歌,則仍然是講述傳統故事、接近口頭詩歌風格的作品。在這類詩歌演唱者中最著名的是女歌星西蒂·賓蒂·薩阿德(1880—1950)。
當代斯瓦希里詩人的代表是蒙巴薩的艾哈邁德·納西爾·賓·朱馬·巴洛。他的詩歌具有與世界上其他早期民族詩歌相似的特點,同時經配樂在電臺上演播又體現出當代特色。他的詩歌由專業歌手在阿拉伯風格的音樂伴奏下演唱。他的詩多屬格言警句;詩人認為自己肩負有政治家、演說家的使命。他在一首詩中寫道:
啊,演說家,來吧,演說!
這就是我,一頭咆哮的雄獅在叢林中怒吼!
斯瓦希里詩歌作為肯尼亞和坦桑尼亞民族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隨著斯瓦希里語確立為民族語言而日益發展,欣欣向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