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原》作品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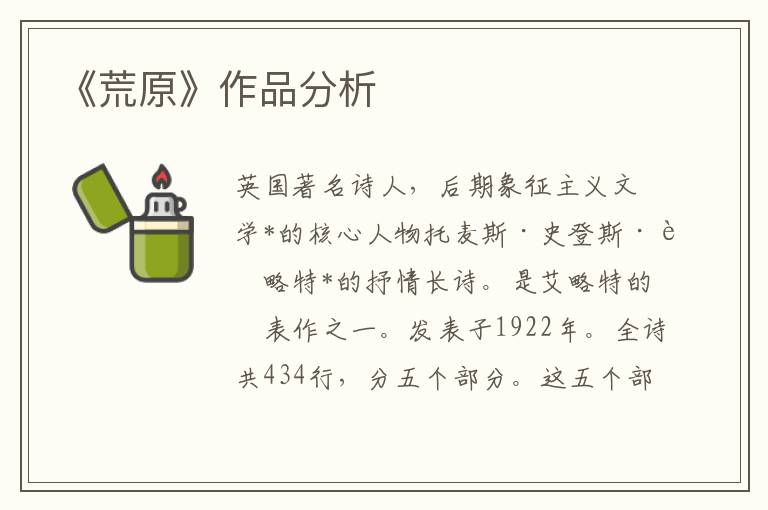
英國著名詩人,后期象征主義文學*的核心人物托麥斯·史登斯·艾略特*的抒情長詩。是艾略特的代表作之一。發表子1922年。全詩共434行,分五個部分。這五個部分的標題分別是:《一、死者葬儀》、《二、對弈》、《三、火誡》、《四、水里的死亡》、《五、雷霆的話》。詩前有兩則副題:一是看見女先知西比兒吊在一個籠子里,她和孩子們的一問一答;一是:“獻給艾茲拉·龐德*/最卓越的匠人。”
《荒原》是艾略特前期的重要代表作品。長詩真實地展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整個西方世界的精神危機,宣揚只有皈依天主教,才能使這個腐敗、荒涼、混亂的社會得以復蘇。長詩恰如一個展廳,把西方世界的絕望、敗壞與淪落的雜七雜八、形形色色的景象披露在讀者面前,對于我們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的方方面面,具有一定的意義。但長詩宣傳天主教的救世思想,似乎只有上帝才能最終拯救這個世界,這卻是一種謊言。長詩第一部分描繪了荒原上的破敗景象:最美好的四月也是殘忍的,這里有破碎的偶象,枯死的樹,到處是恐懼、荒涼、女相士在占卜,倫敦街上的黃霧、人群,邁里海戰的幸存者在一個花園里種下了一個“尸首”,竟然希望它發芽、開花,希望忽來的嚴霜,不要“搗壞了它的花床”。第二部分著重寫西方世界的淪落。詩人把古代女皇克莉奧佩特拉放縱情欲、狄多自殺、鐵盧歐斯強奸妻妹翡綠眉拉和冤冤相報的故事,與現代人的淪落做了對比,指出麗兒的淪落與三個帝王的荒淫無甚區別。第三部分,寫倫敦的墮落與腐敗,表現現代人的無聊與空虛。作者寫到泰晤士河上飄浮的手絹、香煙頭,游玩的“仙女們”走了,留下一片飄浮的垃圾;一個女打字員墮落了,她滿足情人的愿望,自己也了卻了一份心事。帖瑞西斯兩次變形;萊茵河上三個女兒唱著失身、懺悔和怨恨之歌;而這時劫火在燃燒,要把一切罪惡燒盡。第四部分,寫腓尼基老人弗萊巴斯為利欲而墮海身亡的情景,暗示生命之水也救不了人類,人類只有尋求天主拯救才是唯一生路。第五部分,重現荒原上干旱、衰敗的慘景,證明只有“舍己為人。同情。克制”,才能使荒原復蘇。這或許是詩人要找的真正的“圣杯”。
長詩獨特的藝術表現手段,十分引入注目。這首長詩,沒有一個中心情節,沒有一個全詩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它是由眾多的“客觀對應物”,各種引證、意象、幻覺疊合起來,形成了無數個不相關聯的意象的掛幅。這種多意象的疊合正是長詩重要的藝術特征,是詩人“非人格化”、*客觀對應物”理論的重要的藝術實踐。其次是旁征博引,即所謂“征引”。長詩引述、仿制、改制其他作品中的形象或語言片斷是不勝枚舉的。據統計,長詩引述過六種語言,35個作家的56部作品。這些引述,有原文引述,大意引述,意象引述,場景引述,事件引述,但又是經過改造過的屬于作者自己作品中的獨特意象。再次,長詩使用了多義的象征手法。詩中著力描繪的“荒原”的形象,既可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歐洲的象征,也可以是一次戰后西方精神危機的象征,甚至也可以說是一種“原罪”的象征。即如詩中人物帖瑞西士既是奧維德《變形記》中的人物,又是長詩中的人物,可以是自喻,也可指一切冷眼旁觀的詩人,他甚至又是古今一些罪惡的見證人,最后,長詩的韻律也很出色。正如《荒原》譯者趙蘿蕤先生所說:它是“在不規則中有規則,在沒有節奏中有節奏,給人的印象不是舒展、粗獷、自由,而是極其嚴謹,極其豐滿,極有分寸。”
《荒原》是象征派詩歌,甚至是現代派詩歌發展史上的里程碑,是西方文學史劃時代的杰作。它的命意有《神曲》的旨趣,但卻沒有《神曲》的展示新世界的思想的晨光。宗教說教,使這部作品的價值,受到一定的傷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