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灑疆場日彰顯忠義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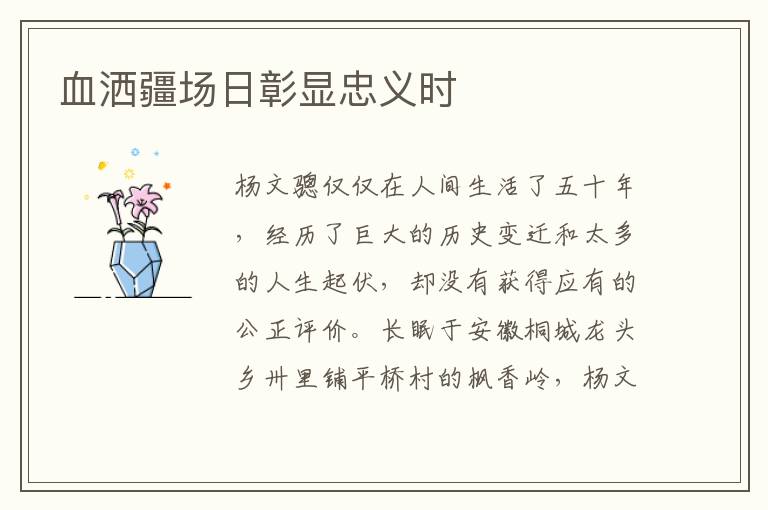
楊文驄僅僅在人間生活了五十年,經歷了巨大的歷史變遷和太多的人生起伏,卻沒有獲得應有的公正評價。長眠于安徽桐城龍頭鄉卅里鋪平橋村的楓香嶺,楊文驄的忠魂沒有能夠回到故鄉貴陽,更期待著后學從歷史傳說的迷霧中認識真正的民族英雄。
楊文驄(1596—1646),字龍友,號山子,別署伯子,貴州貴陽人。人們對于歷史上的民族英雄楊文驄了解無多,論之幾無。所以,他成了寂寞的民族英雄。而對于《桃花扇》中的楊龍友,人們或許并不陌生。因為《桃花扇》中塑造的藝術形象楊龍友與阮大鋮關系密切,混跡于秦淮脂粉之間,又有斷送南明弘光政權前途的大舅子奸臣馬士英,在舞臺上的形象不是光彩照人,而是多有毀損。劇本中的楊龍友,是個快活才子,又是智多星,更是一個老于世故而圓滑的官場丑角。歷史上的楊文驄,確實成為閹黨勢力與復社領袖之間的聯絡人,游走于秦淮脂粉、東林、復社和閹黨之間。《殉節錄》中的議論說,如楊文驄者,抗節亦有可矜,進身究為可議,輕易地將楊文驄踢了出來。所以,學界很少關注這位歷史上真實忠義的民族英雄。即便是書畫藝術、詩歌成就,在書畫史和文學史著述中幾乎沒有提及。原因很簡單,藝術作品中對他的形象塑造影響了學界的深入研究;客觀而復雜的人際關系難以梳理也令學者難下結論。主要原因,在于楊文驄有一個與閹黨余孽阮大鋮關系密切并對南明弘光政權滅亡有重大責任的大舅哥:在《明史》進入“奸臣傳”的馬士英。“以士英故,多為人詆”。近年,對于楊文驄的書法、繪畫、詩歌研究,有不少的論。然而,僅僅是論定其藝術而已。即便是白堅先生的《楊文驄傳論》,也只是梳理了他的書畫風格與成就,并肯定了他在詩歌史上的地位:“楊文驄也是一個優秀的愛國詩人和山水詩人”,“在詩歌史上,也應該有他的席位。”楊文驄在歷史上應有的民族英雄定位,卻未見學界闡述。
一、 徘徊蹉跎 尋找人生定位
簡單說,楊文驄的人生幾乎是在徘徊選擇中蹉跎而過,直到南明政權建立,方得到最后的定位,才完成了自己的歷史形象塑造。換一種說法,是楊文驄多才多藝,修養全面,在多個領域均有深厚的造詣。但是,在楊文驄的內心深處,最理想的目標并不是詩文書畫有所成就,而是立馬橫刀,馳騁疆場,建功立業,存名青史。然而,現實是楊文驄蹉跎歲月中,以書畫詩文得到時人的贊許,成為晚明杰出的書畫家、詩人。楊文驄的人生定位,是徘徊于藝文與科舉之間,又崇尚武藝,好弓馬劍術,并未致力于制藝一項。但為了生存,又必須入仕取祿。
陳子龍《楊龍友洵美堂詩集序》:“予交龍友幾二十年,初見其繪事,上掩李黃,近匹沈董而服其藝。已,見其詞章藻麗,歌詠明逸而遜其敏。既見其芝田永嘉之治,行清惠可師而式其政。又觀其挽強馳駿,矢無虛發,而畏其勇。及與談濟世之事,智略輻輳,意思宏深而嘆其未可測量。”而更重要的,是陳子龍希望楊文驄能夠“一當匈奴,懸郅支之首,焚老上之庭,然后回師南指,掃清河洛”(陳子龍《安雅堂稿》)。在陳子龍眼里,楊文驄就是文韜武略足以經營天下的能人,而其最高境界則是“濟世”,而當今之世最需要濟的,就是外殲強敵,內平叛亂。而能夠“濟世”,首先需要一個恰當的空間。于是,楊文驄與同時代的書生一樣,讀書、科舉、入仕。
楊文驄自幼聰明穎慧,志向遠大,學文習武,詩文書畫,無不通曉,挽弓擊劍,身手不凡。但科舉失利,沒有得到名正言順的進士出身。
楊文驄出生貴陽,成長于貴陽。七歲時其父親楊師孔任山陽縣(江蘇淮安)令,楊文驄隨父遷居山陽,從此與江蘇結下不解之緣。但他的青年時期,主要在貴陽度過,并于萬歷四十六年(1618)在貴陽參加鄉試,成為舉人。次年北上京師,參加禮部會試,失利,返回貴陽。天啟二年(1622),因貴州安邦義發動叛亂,兵圍貴陽,27歲的楊文驄參與保衛城池的戰斗,沒能北上參加會試。次年,楊文驄舉家遷居南京。從此,除崇禎四年(1631)丁父憂,楊文驄每逢會試之年即前往京城應試,直到崇禎十年會試失敗,徹底離開科場。功名失利,并非楊文驄才藝知識不夠,是準備不夠對路,也不夠充分。從中舉之后的行實看,楊文驄的大量時間并沒有用于準備科舉考試。因為按照明代科舉制度,題目來自“四書”“五經”,釋義遵守“集注”“大全”,行文按照“八股”套路,對于崇尚揮灑自如的楊文驄,自然不是強項。且楊文驄興趣廣泛,詩文書畫,歌舞宴席,又占去大量時間和精力。更重要的是楊文驄志在四方,上馬擊劍,下馬畫陣。如果科場、疆場讓他選擇,更著意后者。于是,徘徊中尋找人生的定位,又不得不為現實的生存考慮。
崇禎四年之后,由于生存問題首先必須得到解決,楊文驄必須爭取一份俸祿以養家糊口。藝備文武,無處請纓馳騁;心懷天下,蹉跎天子門外。而父親過世,家境陵替,楊文驄必須謁選謀職,以獲取薪水維持日常開銷。崇禎七年七月,楊文驄正式任職,為南直隸松江府華亭縣教諭,為時五年。
在華亭任教諭的過程中,楊文驄又參加了一次會試。崇禎十年的會試,復社有諸多名流中進士,狀元劉同升,榜眼陳之遴,探花趙士春均來自復社,復社的陳子龍、錢肅樂、胡夢泰、揭重熙、夏允彝、施鳳儀、蔣棻、包爾庚、劉憲章、秦鏞、周銓、張明弼、蔣鳴玉、錢朝彥、何宏仁、倪仁禎、熊人霖、劉大年、余飏、吳之琦、王追骎、余士瑋、王泰徵、趙士驥等數十人也都中了進士,但沒有楊文驄。原因何在?從楊文驄在華亭的社會活動考察,可知他根本沒有用時間精力去準備八股制藝。這是楊文驄最后一次參加會試,此后再也沒有北上京師。在這五年的時間,楊文驄既要吟詩作畫,又要結交大量的社會名流,還要從事教育工作,還有騎射等等,很是忙碌,不會有多余的時間致力于科考。
其實,任職教諭,只是擔任了政府官僚體系中的小吏,沒有正式的品級。只有正式擔任縣丞、主簿,才是入流的從九品或稍高的入流官員。按照明代的慣例,應該是三年考選量移,即換個地方任職,考滿方能遷升。“考滿之法,三年給由,曰初考,六年曰再考,九年曰通考”。楊文驄在華亭是超期履職,又超常提拔為青田縣令。而這兩次超常規的任職,雖原因難以考索,都與他的大舅子馬士英并沒有什么關系。因為馬士英在崇禎五年起就罷職流寓南京,直到十年后起復,不可能幫到這位妹夫。最大的原因,就是楊文驄超常的行政能力和在松江的杰出表現。
所以,現實中的楊文驄是晚明徘徊與藝文科舉及文武之間,以其才華,而成為晚明書畫大家,有吳門畫派的柔媚,又有關仝、范寬的山水骨力,行書柔媚中不乏剛勁,草書遒勁中透露飄逸,給人以不能束縛的力量。又百無聊賴以詩名,成為晚明杰出的詩人。《洵美堂詩集》九卷,存詩462首。莫友芝《黔詩紀略》中,也收楊文驄詩歌325首,分為三卷。而現存作品多為38歲以后所寫,早年詩歌基本無存。楊文驄在藝文科舉與文武之間的徘徊蹉跎,等來的是明朝滅亡,清朝南下的歷史巨變,也迎來了他完成自我塑造的最后時刻。
如果說游走于科場疆場之間,是楊文驄的一種人生徘徊。結交正人君子,也沒有拒絕奸佞小人,是楊文驄人生態度的又一種徘徊,飄忽于正邪之間。
楊文驄的人格本質,屬于清流,具有貞潔之史的氣概豪情。崇禎十一年七月,他們聚集于無錫的顧杲家中,分韻賦詩。吳應箕的《周勒卣(立勛)楊龍友(文驄)集子方(顧杲)兼山堂分得十四寒》,表現了他們的志趣豪情:
七月青林烈日團,高堂客聚亦生寒。
偶然澤國琴樽共,遂作龍津氣象看。
雅道定知刪薈蔚,老成今復見波瀾。
相期莫訝吾曹在,赤白何人制探丸。
從楊文驄結交東林遺老、東林后裔、復社領袖的情況看,楊文驄得到了這些人物的欣賞與敬重,并非偶然,而是他們在政治傾向上、情感志趣上完全一致。在楊文驄的朋友中,有東林前輩錢謙益,更有長者孫承宗,而從天啟三年(1623)到崇禎七年的十一年時間,楊文驄活躍于南京,而楊文驄此間的交游人物,主要有復社文人張溥、張采、吳應箕、顧杲、陳子龍、周立勛、夏允彝、徐孚遠、方文等。他們或聚集于松江,或吟哦于梁溪,意氣相投,互相激發。
上述復社領袖人物中,張溥不僅是復社的創立者與領袖,更是天下文人的精神依歸。而吳應箕、顧杲等人在與閹黨余孽阮大鋮的斗爭中勇往直前,并在南明弘光政權滅亡之后起兵抵抗清軍的南下,成為明清易代之際的忠烈之士。
然而,楊文驄事實上又與奸邪人物來往密切,甚至有意調和復社領袖、名士與閹黨余孽之間的關系,也是不爭的事實。楊文驄的內兄馬士英,崇禎五年因聚斂行賄被奪官流寓南京。馬士英的同年摯友阮大鋮以名列閹黨,避居南京。于是,兩人沆瀣一氣,私交甚密。因為內兄的關系,楊文驄與阮大鋮也過從甚密,并試圖將復社名士侯方域與阮大鋮拉近。阮大鋮的動機是化解與東林的矛盾,為以后的復出創造條件。而侯方域雖然是年輕的復社名士,更在背后有個東林名宿的父親侯恂。從這層關系,可以看出阮大鋮結交侯方域的用意了。楊文驄正是兩人之間的穿針引線者,而針線就是秦淮美女李香君。這段故事,被孔尚任詳細地再現在《桃花扇》中。由此看,楊文驄是不拘小節的君子,而其弱點,也正在于此。“文驄善畫,有文藻,跌宕風流,豪邁自憙。好推獎士類,干士英者緣以進,故為世所詆。其死也,眾論亦許之”(徐鼒《小腆紀傳》,中華書局1958年版)。所以,只有最慘烈的壯舉,才能完成他歷史上民族英雄形象的自我塑造。
(江蘇省社科基金項目“晚明文化生態與復社運動”,項目編號:13ZWD018)
(作者單位:蘇州科技學院人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