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國恩《苦力》東方文學名著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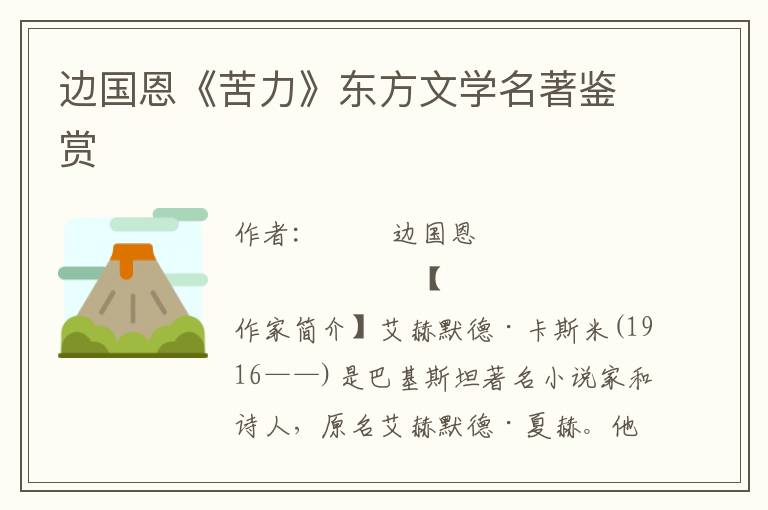
作者: 邊國恩
【作家簡介】艾赫默德·卡斯米(1916——)是巴基斯坦著名小說家和詩人,原名艾赫默德·夏赫。他的作品現實性強,鄉土氣息濃郁,被譽為“旁遮普的鄉村歌手”。
1916年,卡斯米出生于旁遮普省薩勒古特區安卡村的一個鄉村小官吏家庭,祖上屬于名門望族,但后來家道中落。他的童年是在沒有歡樂的困苦的農村生活中度過的,后來,靠一位好心的親戚資助才得以進入旁普大學,于1935年畢業。
畢業后,他當過公務員。二次世界大戰后又成了保衛和平的著名戰士,印巴分治后的1949年,他當選為巴基斯坦進步作家協會的書記,并主編過《銘刻》、《今日報》等報刊雜志。
卡斯米小說的主要題材,一類是以抨擊阻礙社會發展的舊風俗、舊習慣、舊傳統和社會上的不平等為其主流的,主要有《斧子》、《買石板的男孩子》、《盜竊》等;另一類是反對殖民主義統治,譴責英國殖民主義分子,支持民族獨立和解放,同情勞苦大眾的疾苦為題材的小說,主要有《金色的小圖章》、《祝你幸福》、《苦力》等。
卡斯米的詩歌要比他的小說更有名,他素有“旁遮普的鄉村歌手”之美稱。其詩歌創作大體可分為四類:其一是抒情詩,充滿失望、失戀和哀傷,是充滿感傷情調的悲歌;其二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詩歌,具有代表性的詩作為四部詩集:《心的跳動》、《淅瀝的雨聲》、《壯麗與美》、《花的火焰》等;其三是抨擊黑暗勢力,滿懷信心迎接世界的“新紀元”,主要作品有《那里與這里》、《忠實的大地》等;其四是描寫鄉村生活和風上人情的抒情小詩。
卡斯米的詩歌形式主要有敘事詩、自由詩,法國式的八行詩。除上述小說、詩歌作品外,他還有四部兒童文學作品和一部評論集。
1963年,他以詩集《忠實的大地》榮獲基爾迪巴基斯坦作家獎。無論是詩歌還是小說,他的作品都以細膩的描寫,濃郁的鄉土氣息和強烈的現實性著稱。
《苦力》,馮金辛譯,選自《金頭花》,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出版。
【內容提要】一個漆黑的冬夜,我在拉瓦爾品第人煙稠密的、狹窄的街頭巡邏。因為凍得手足麻木,我便鉆進了城郊一家我喜歡的又小又舊的館子休息。在那里,我一邊喝著茶,一邊諦聽著坐在四周的苦力們的談話。
苦力們在興致勃勃地聊聊天,說幾句笑話,笑上一陣,或者在長凳上躺一會,或者在鐵椅子上打著拍子唱唱歌。而當火車馳近的聲音傳來的時候,他們就拿起自己的青銅棍子扛在肩上,如飛地奔往街上,前去碰碰運氣。苦力們漫無邊際地議論著拉瓦爾品第的大飯店,那里一碗清茶的價格和分不清到底是飯店還是陵墓的某地。
我終于加入了他們的談話。
“哥兒們,你們怎么啦,是為了開玩笑還是怎么的,紅號衣上釘了白扣子?”
穿燈籠褲的小伙子替大家回答:
“白扣子便宜得多唄。”
以后又是議論家庭、老婆、鄰居。“不知是誰,不小心,從桌上打掉了一只茶碗”,茶館白沙老板看在我的面上饒了他們。
苦力們對我有了好感。我呢,也喜歡在這家小館子里消磨時間。每天巡邏之后到那兒去已成了我的習慣,若是不去,整天我都會心緒不寧,覺得無比的煩悶。
有一天,天氣特別冷,我就拐進了火車站旁邊的這家小館了。“我凍得冰冷的身體依然直打哆嗦,館子里除我以外只有苦力,他們在遠遠的一個角落里靠墻蹲坐著打盹。”
我走到一個身穿一條過長的燈籠褲的苦力跟前,知道他叫穆罕默德,是從阿托卡郊區來的。
我后來常和他聊天。他很聰明。我確信,這個小伙子要是能受教育,他無疑會成為偉大的詩人,毫不夸張地認為他是拉瓦爾品第所有苦力中最出色的思想家,不亞于迦梨陀娑、莎士比亞、彌爾頓、歌德、伊克巴爾等人。只因為他是苦力,因此無人知曉他。
他很有學問,也懂禮貌,心眼又好,怕我的腳踏車被雨淋了。把它推進屋子里,放在墻邊。
我問他,為什么那些苦力沒來?
他說,他們沒有雨衣,沒有遮蓋的布,要是他們這些可憐蟲凍死了,誰供養他們挨餓的母親、姊妹、妻子、兒女呢。
當問及他為什么在這樣壞天氣里還出來時,他說:“整天呆在家里,心里怪悶的,決定來這兒聊聊天把時間打發過去。”
他拿出錢來要了一壺四碗的茶,請我喝。我心里很是過意不去。一個要在背上扛三四滿重的東西,要氣喘吁吁地走上好幾里路才能賺到一個安那的人,怎么會想到把一個安那白白送給警察呢?我問他為什么這樣?他說:“您是個很好的人,軍士老爺,您常講那些好事情……總之,我很喜歡您。”
我同他講了為什么警察逮捕罪犯盜賊的道理。他信服了。在與他的交談之中,才知道穆罕默德·丁掙的錢很少,家中有一個老娘和一個沒有出嫁的姐姐。白天他和家人呆在一起,晚上來等火車。因為晚上車站上小工少一些,乘客呢,在晚上也會比規定的價格稍微多給幾個。老娘和姐姐不放心他,每天都“白白犧牲了自己的睡眠”。小伙子每夜要接七八班火車,有八九個安那的收入。正在與我聊天的穆罕默德·丁,一聽到火車聲響,他便“大聲叫醒自己的伙伴法茲爾·丁和希達雅特·汗,于是三件紅號衣向著敞開的大門奔去,消失在狂風肆虐的可怕的黑暗中”。
那一晚,我睡得很少。我在想著自己的新相識。這些貧窮的苦力是把自己的青春葬送在難以扛負的沉重的貨物下面了——這些勤勞的人們是不是知道什么叫愛情?他們骯臟的紅號衣里那顆心曾經為愛情跳動過嗎?那些為了金錢而壓榨自己親鄰的下賤家伙,難道還不曾對自己聲色犬馬的嗜好感到厭倦?
第二天,我巡邏后到小館子里去的時候,遠遠地就看見穆罕默德·丁在門口等我。他照例把我的自行車推進屋去,我們照例地交談著。這次談到火車站長叫他的孩子騎在穆罕默德·丁的身上,不但不給錢,一不高興還要叫喊:“剝掉你的號衣!”“扣留你的號碼!”“要送你去坐牢!”小伙子還給我講述了昨天下大雨時火車站長讓他把一筐水果送到他家去的事。這一夜一個子兒也沒掙到,可是回到家中,“看到挨餓的老娘和姐姐,我哭了一夜,……住的房子屋頂上好多地方都漏了,……我們三個人爬到一個犄角里,冷得緊緊地擠在一塊,我的頭枕在娘的腿上,一只手放在姐姐的膝上……忽然有幾滴熱水掉在我的脖子上。這不是雨,……是眼淚”。
還要往下哭訴去的時候,火車開進車站。“穆罕默德·丁一躍而起。幾件紅號衣像火光似地飛出了大門,黑黝黝的房間里籠罩著死一般的寂靜”。
這次談話后,一連四天我沒有見到穆罕默德·丁了。原來是他姐姐得肺炎死了。他沒有錢買藥治病,眼巴巴地看著姐姐斷了氣。穆罕默德·丁到市場去掙幾個錢買口棺材把她葬了。
即使這樣,他還是從口袋里掏出了僅有的一個安那,要了一壺四碗的茶!
火車又到了,穆罕默德·丁,小聲說對不起后,就和別的許多紅號衣飛快地向門口跑去,消失在夜的黑暗里。
我面前放著的那碗清茶,不知什么時候起就已經涼了。
【作品鑒賞】“家庭”這個人類社會的細胞,多么親切,又多么珍貴。然而在舊社會,每個家庭卻不一樣:有幸福的,也有不幸的。巴基斯坦著名小說家卡斯米所著短篇小說《苦力》中的主人公穆罕默德·丁的家庭的的確確是不幸的。作品宛如一幅筆力蒼勁,色彩濃重的水墨畫,透過“我”所耳聞目睹的種種事實,把下層人民勤勞、憨厚、慷慨、誠實的美好品德展現于讀者面前,清晰看到主人公家庭的貧困不堪,身上的道道傷痕,斑斑血跡,從側面窺見了吃人的舊社會的兇殘以及下層人民是如何在血泊中掙扎和煎熬的,看到了他們為了生存,在漆黑的夜里,穿著“紅號衣飛快地向門口跑去,消失在夜的黑暗里”。一想到這些,讀者的咽喉便哽咽了,宛如堵塞了一個硬塊,使你喘不過氣來,頓時升騰起一腔怒火;同時也不免為主人公的遭際滾下顆顆熱淚,滴在你剛剛看完的書上。
小說采用了第一人稱的直接敘述方式,以“我”的所見、所聞、所感、所想結構而成。故事中的“我”,既是夜間“拉瓦爾品第人煙稠密、狹窄的街道”的巡警,又是苦力們的新朋。這樣,不僅給讀者以親切、真實之感,而且還自然溝通了主人公、讀者、作者之間的情感世界,使之得以心靈交匯。小說伊始,“我”并沒有急于講故事,交代主人公如何如何,而是寫在那無盡無休的“漆黑的冬夜,陰雨綿綿”的日子,躲進小茶館是多么“舒服”。緊接著,作者就把“我”在小茶館聽到、見到的一切都一五一十地告訴了讀者。信不信由你,反正這是事實。在與苦力們聊天、喝茶時,作者并未講出什么引人入勝的故事,而是力求通過藝術手段,如對話、描寫、動作、肖像等,讓讀者感受故事的真實性,從而深刻再現主人公的苦難身世,以此打動讀者,喚起人們對處于水深火熱之中的下層人民的同情和憐憫,對舊社會的不滿和憤恨。
小說情節簡單,不枝不蔓,集中凝煉,通篇沒有多余的描寫。作品三次寫“我”的所見所聞是按時間順序串聯起來的,并加以精心剪輯而成,從而構成主人公穆罕默德·丁的苦難史和身世錄。對“我”與主人公三次交談,作者并未平均使用筆墨,而是有主有次,有詳有略。譬如第一次,“我”初進這家舊的小茶館時,只是以眼睛所及,看到的桌子、椅子,水煙筒、煙斗,老式燈籠,以及早已在這里的苦力們,爾后便聽到他們的議論和穿燈籠褲的那個苦力——穆罕默德·丁;第二次寫“我”認出了穆罕默德·丁,他還要了“一壺四碗的茶”請我喝。這次“我”與他談的問題較為集中,知道了他的名字,哪里人氏,家中的簡單情況等;而第三次,作者巧設懸念:“這次談話后,一連四天我沒有見到穆罕默德·丁”。原來主人公的姐姐得了肺炎,因無錢醫療死了,將故事推向高潮,同時主人公的思想境界,慷慨大方的美好品質也得到升華:照樣從口袋里掏出一安那的錢,要了“一壺四碗的茶”請我喝。第三次雖然是高潮,但并非重點,重頭戲在第二次交談。在我們看來,三次造成的反差較大,作者用意則在于讓親愛的讀者自己去思考和回味。尤其是篇末,主人公的姐姐死了,老娘挨餓,他自己又不得不在漆黑的夜晚離開“家”,而同“別的許多紅號衣飛快地向門口跑去,消失在夜的黑暗里”。
暗喻也是作者匠心獨運。小說多次寫“一只蜥蜴”的活動:“墻上傳來刺耳的沙沙聲,一只蜥蜴從墻上爬到屋頂,消失在那個漆黑的裂口里”。爾后又寫“墻上,沙沙地響起來,又爬出一只蜥蜴躲在屋頂底下……”這多么像我們的主人公在漆黑的深夜出出進進于破舊的、黑暗的小茶館,為生存,為一家三口人的生活而奔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