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锳先生治學方法的會通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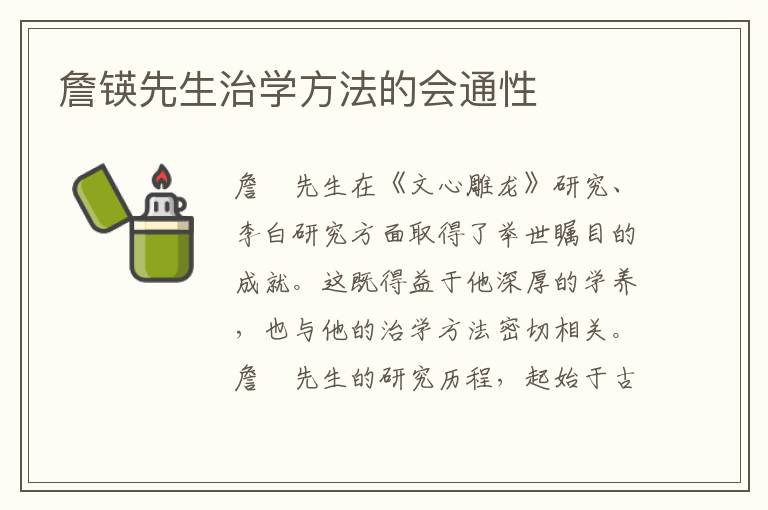
詹锳先生在《文心雕龍》研究、李白研究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既得益于他深厚的學養,也與他的治學方法密切相關。詹锳先生的研究歷程,起始于古典文學研究,后轉向心理學研究,最終回歸古典文學研究。詹先生在古典文學、心理學兩個學科的成就,目前只有前者得到了研究。這主要是由于詹先生的心理學研究尚未充分展開,即被終止,沒有留下足以傳世的心理學研究成果。但是,詹先生在這兩個學科的研究方法,卻在某些層面存在會通性。詹先生早期的古典文學研究經歷對其心理學研究存在影響,而后者又對詹先生后期的古典文學研究產生了潛在影響。綜合這兩個學科來觀察詹先生的治學方法,有助于我們理解他的治學方法的內在理路。
從詹先生的治學之路來看,他1934年考入北京大學,畢業后在高校任教,至1948年出國留學,這十四年間,他的研究對象是古典文學。詹先生到美國留學,先學比較文學,后出于實學報國的目的,改學心理學,并先后獲得心理學碩士和博士學位。1953年詹先生回國,由于政治環境的原因,他的心理學實驗和研究屢遭阻撓。在1958年全國心理學批判中,他成為被批判的重點,被停了課,醫學心理學實驗也夭折了,至此,詹先生對心理學喪失了信心。詹先生出國之前寫成的《李白詩論叢》和《李白詩文系年》卻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先后于1957年和1958年出版,從而點燃了他對古典文學的希望之火。詹先生于1961年從天津師范學院教育系調入中文系,十二年(1949—1961)的心理學研究之路,畫上了句號,而一段輝煌的古典文學研究之路由此開始。
詹锳先生早年的古典文學研究,主要集中在李白研究上。1940年初,詹先生在西南聯大中文系任助教,開始研究李白,并且在1948年出國留學前就已經完成了《李白詩論叢》《李白詩文系年》兩部書稿。尤其是《李白詩文系年》,表現出詹先生扎實的文獻功底。他對李白詩文的編年,從李白的全部文獻出發,進行梳理辨析。
詹锳先生這種從全部文獻出發的編年、詮釋功夫,對他后來的心理學研究有正面影響。他對巴甫洛夫心理學特點的研究,就是受到了這種方法的影響。在詹先生的心理研究成果中,有一篇名為《巴甫洛夫心理學觀點的歷史探討》的論文尤其值得注意,因為在這篇論文中,詹先生以巴甫洛夫研究為例,論述了他研究心理學的方法。
在中蘇心理學家討論這類問題的文章里有一個比較普遍的現象,就是作者先有自己的主張,然后引用巴甫洛夫的一句話甚至半句話,作自己的言論的注腳。凡是和自己的意見相合的地方,就盡量的征引并解釋;而和自己的意見不相符合的地方,就一筆帶過甚至一筆抹殺。于是甲也引巴甫洛夫,乙也引巴甫濟夫,而大家都對不起頭來。針對這種趨勢,我覺得有把巴甫洛夫全部和這方面有關的言論進行分析的必要。
詹先生指出中國和蘇聯的心理學家在引用巴甫洛夫觀點時,都存在只抓只言片語的現象,導致對巴甫洛夫的理解存在主觀片面性,而要準確理解巴甫洛夫的心理學觀點,就必須從他的全部論著出發。詹先生指出:“高級神經活動和高級神經活動生理學這兩個名詞是巴甫洛夫提出來的,對于這些名詞的解釋只有從巴甫洛夫的著作里去找才會正確,否則你有你自己的一套解釋,我有我自己的一套解釋,打著巴甫洛夫的招牌,而販賣自己的藥,這類問題就永遠沒有得到解決的一天。”從全部著作出發研究巴甫洛夫心理學觀點,具體應該如何操作呢?詹先生指出:
我在這里不愿指明中蘇心理學家誰是誰非,而只是用一個笨法子,把我在巴甫洛夫的經典著作中所看到的,以及其他蘇聯心理學家的論文或講稿中引用巴甫洛夫的話,凡是和心理活動和心理學有關的,都把它大體按照先后的次序排列起來,探索一下巴甫洛夫究竟對于心理活動和心理學是怎樣看法,他在一生中前后對于這類問題的提法是否有演進的痕跡可尋,并說明巴甫洛夫一生在這方面的見解是否前后矛盾。
詹先生說的“笨法子”是將巴甫洛夫的全部論著大體按照先后次序排列,對之進行編年、詮釋,這與他早年研究李白詩文系年的方法相似。通過對巴甫洛夫全部論著的編年排序,詹先生全面探討了巴甫洛夫的心理學觀點,并進而研究巴甫洛夫心理學觀點在時間序列上演進的痕跡。詹先生把巴甫洛夫的心理學觀點分為四個時期進行詳細考察,指出前兩個階段(1914年以前)巴甫洛夫重視生理學而鄙視心理學,第三個階段(1916-1927)他才明白心理學也可以研究高級神經活動,第四個階段(1927年以后到巴甫洛夫逝世)他才提出心理學和生理學“結婚”的主張。巴甫洛夫的心理學觀點有一個發展的過程,蘇聯現代心理學家對于心理活動的看法和巴甫洛夫晚年的見解不盡一致,其中不乏對巴甫洛夫的誤讀。究其原因,正在于他們沒有從巴甫洛夫的全部著作出發。詹先生通過編年研究的“笨法子”,整體性探討了巴甫洛夫的心理學觀點,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結論。
由此可見,對研究對象的全部文獻進行編年研究,在詹先生的研究經歷中是一以貫之的方法,并不因為古典文學和心理學是不同的學科而加以改變。事實證明,詹先生使用這種研究方法,取得了學術研究的成功。
詹锳先生十二年的心理學研究經歷對他后期的古典文學研究也有很大影響。如果我們把人的一生看作一個整體,曾經的經歷奠定了人們未來的行為方式、思維習慣、審美喜惡的基本維度。1961年以后,詹先生由心理學轉向古典文學研究,他的思維習慣、研究方法,在某些層面具有延續性。我們不應忽略心理學研究經歷對其古典文學研究的潛在影響。
詹先生從心理學轉向古典文學研究之后,他談治學方法,談的最多的是“科學方法”這四個字。從他所受的科學訓練來看,主要是心理學的研究經歷,賦予了他“科學”的視野和方法。
詹先生在美國留學期間,側重于研究閱讀心理學和心理統計,其中閱讀心理學研究閱讀活動中的各種心理現象及其規律性,包括閱讀過程的模式,詞的認知,句子理解,篇章結構分析,認知監控,動機及社會因素對閱讀的影響等問題。顯然,閱讀心理學有助于對文學作品的分析。這種心理學的研究背景,潛在影響著詹先生的古典文學研究。
詹先生對古代文學作品的研究,注重心理分析。詹先生《古典文學研究雜談》指出:“研究一部文學作品,特別是一首詩詞,我愛作心理分析;對于一個作家,我愛作歷史探討;對于某一作家的作品,我愛作系年的工作,看看這篇作品是在哪一年代寫的,當時的社會背景如何,作者的閱歷如何,這就涉及到歷史范疇了。文學作品本身固然不是科學,對于文學作品的研究卻是科學,研究文學要有科學的頭腦,才能發現問題,解決問題,這樣就不純粹是在那里搖頭晃腦,擊節嘆賞,而是要從美學方面、語言結構方面、歷史背景方面、作者心理方面,說出一個所以然來。”
詹先生對古代文論的研究,也注重運用心理學知識進行探討。例如《文心雕龍·神思》“窺意象而運斤”,詹先生《文心雕龍義證》注曰:
“意象”,謂意想中之形象。《老子》:“惚兮恍兮,其中有象。”《韓非子·解老》:“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易·系辭上》:“圣人立象以盡意。”王弼《周易略例·明象》篇:“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生于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在西方心理學中,意象指所知覺的事物在腦中所印的影子;例如看見一匹馬,腦中就有一個馬的形象,這就是馬的意象。其所以譯為“意象”,是因為和王弼的解釋類似。
詹先生對于“意象”的注釋,先引《老子》《韓非子·解老》《易·系辭上》以及王弼《周易略例·明象》的相關界定,指出“意象”就是意想中的形象。接著,詹先生又指出在西方心理學中,意象指所知覺的事物在腦中所印的影子,與中國哲學中的意象含義類似。他運用西方心理學知識就“意象”問題的中西比較,使得意象的內涵變得通俗易曉。
又例如《文心雕龍·神思》“萌芽比興”,詹先生《文心雕龍義證》注曰:
運用形象思想,不能不采比、興等手法。可見“萌芽比興”實際上已接觸到如何運用形象化的藝術手法來表達思想感情的問題。《比興》篇說:“詩人比興,觸物圓覽,物雖胡越,合則肝膽。”文藝創作要通過各種創造性的想象活動,如心理學上講的類比連想(約相當于“比”)、接近連想(約相當于“興”)等等,把本來不相關的東西(“物雖胡越”)聯系融合在一起,創作出優美的藝術形象。
詹先生指出中國文論中的“比”類似于心理學上講的類比聯想;“興”類似于心理學上講的接近聯想。他對“比興”的心理學解釋,令人耳目一新。
詹锳先生由心理學轉向古典文學研究之后,從后者的研究需要出發,對前者依然有所關注。例如詹先生《文心雕龍義證》“主要引用書目”,列出了“《文藝心理學》,朱光潛撰,《朱光潛美學文集》第一卷,上海文藝出版社版”,這證明詹先生的研究轉向之后,對于心理學仍保持著一定的關注,甚至在自己的古典文學研究中加以引用。
詹锳先生治學方法的會通性,當然是建立在他對心理學與古典文學這兩個學科的研究基礎之上。二者的會通,既體現了詹先生潛在的思維習慣、研究方法的延續性,更是他主動的學術追求。詹先生主張跨學科研究,他在《古典文學研究雜談》中指出:“我的知識是大雜燴,不取一家之言,也不是從一個角度出發,我希望能做到實事求是,能采取各家之長。唯其學得比較雜,不限于一種專業,我在發現一個問題時,能從各個角度來探討,從不同的專業來研究。”
詹先生跨學科的研究方法,是他追求創新的結果,也是對當時單一研究方法反感的結果。詹先生留美之前,在大學中文系任教多年,發現古典文學教師中頑固不化的腐儒很多,而且門戶之見很深,胸襟非常狹隘,這和他們知古而不知今、知中而不知外有關,因此詹先生主張打破學科界限以及中西門戶之見,從而觸類旁通。詹先生《自傳》說:“我不崇拜古人和洋人,也不迷信名人,常常想在科學研究中提出自己的看法,而這些看法往往雜糅古今中外,不限于一種學科。”觸類旁通是詹先生跨學科研究的反映,也是他的治學方法的重要特點。
這種觸類旁通不僅表現在心理學與文學研究的會通,從更大的范圍來說,是一種比較的視野。詹先生曾有志于到美國學習比較文學,雖然后來改換專業,但中西比較的視野始終存在。詹先生《文心雕龍義證》除了引用中國古代經史子集四部文獻來注釋《文心雕龍》,還廣泛吸收了今人的相關研究成果,該書末尾列出了“臺灣有關《文心雕龍》研究書目”“日本書目”“匈牙利英文書目”,證明詹先生的閱讀范圍極廣,涉及他所能找到的關于《文心雕龍》的全部資料。例如《文心雕龍義證·通變》對劉勰“綆短者銜渴,足疲者輟涂”兩句,詹先生引用了臺灣張立齋《文心雕龍考異》、日本斯波六郎《文心雕龍范注補正》的相關詮釋,以資參考。《文心雕龍義證·附會》的結尾,詹先生引用了亞里斯多德《詩學》、賀拉斯《詩藝》、郎吉弩斯《論崇高》,以及朱光潛《西方美學史》的相關評述。詹先生認為劉勰的“風骨”論與郎吉弩斯的《論崇高》相類似,認為風骨屬于陽剛之美的藝術風格,這是前人所未發的。
“觸類旁通”重在“通”,通方知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西方理論、學術名詞大量引入中國,學者們被西學話語輪番“轟炸”,甚至有了“失語癥”的擔憂。但是詹先生的古典文學研究,卻并沒有被各種理論、術語“綁架”,西學的優點早已被他“中國化”,渾融在他的研究之中,如水中鹽味,色里膠青,渾然一體。詹先生的古典文學研究既不唯古,也不唯今,他會通古今中外,本著“無征不信”的理念,取得了巨大成就。正如詹先生《古典文學研究雜談》所說:“我對于辭章之學的理解,也常常是通過考據來論證,總是‘無征不信’。我覺得在當前的研究古典文學,一方面要打破傳統的辭章之學那一套,一方面也不要把古人的文學理論現代化,把古人美化成現代人,或者是用現代的標準來衡量古人,那樣都不是研究學問實事求是的態度。”
詹锳先生治學的科學態度和會通意識,對當下依然具有重要啟示意義。古典文學的研究,需要我們站在像詹先生這樣優秀學者的基礎上,往前推進。詹先生留下的治學方法,是一筆寶貴的遺產,值得我們認真總結和反思。
(作者單位:河北大學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