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文學古籍如何結合“非遺”傳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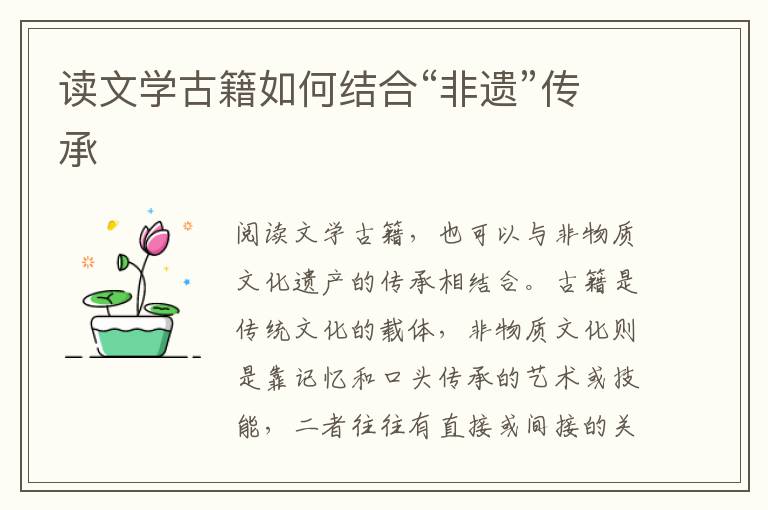
閱讀文學古籍,也可以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相結合。古籍是傳統文化的載體,非物質文化則是靠記憶和口頭傳承的藝術或技能,二者往往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我在閱讀宋元話本的時候,就借助于聽書的經驗,解決了一些困惑的問題。現存的話本或詳或略,或雅或俗,總的說都不會是實況錄音的記錄。因此有的被認為是擬話本,如魯迅對《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和《宣和遺事》的判斷。有人認為話本只是故事的代稱,如日本的增田涉等學者。還有人不承認宋元話本的存在,認為都是明代人改寫的小說。其實,說話人一般有底本,自古以來都是如此。北方的評書藝人,把提綱式的簡本叫做“梁子”,把語錄式的繁本叫做“冊子”,但也不會是實況的記錄。如現代評書名家劉蘭芳播講《岳飛傳》的時候,每天要寫上萬字的稿本,但還是要加上許多臨場發揮。我在參觀蘇州評彈博物館的時候,注意到收藏的彈詞話本,一般只有唱篇,沒有表白;有的雖有表白,也很簡略。也有已整理成書的,一般也不像場上說唱的那么詳細生動。
當然,也有老藝人自己整理成比較詳備的底本,或徒弟繼續加工的繁本,那是很少見的。例如蘇州評話老藝人陸耀庭和顧宏伯,都有說《三國志》的腳本,是自己編寫的抄本,都把一部分腳本送給了學生王忠元。王忠元自己又整理了一個腳本。2015年5月18日,王忠元遺孀華琦把三種腳本都捐贈給了蘇州評彈博物館,成為一時佳話(何兵《留住名家珍貴史料,三部手稿展現戲癡情懷》,據《古代小說研究網》轉載2015年5月20日《姑蘇晚報》)。師父整理了自己的底本,最后送給了徒弟,這是曲藝界常有的事,有些話本大概就是這樣流傳下來的。因此就有了傳承性和變異性的特征,形成了世代累積型的作品。
另一方面,我們還要注意到宋元時期的特定背景,文化重心逐漸下移,特別是元代一度停止科舉,文人沒有出路,走向民間,出現了不少書會才人。他們為藝人編寫腳本,雜劇、散曲是大宗的,都見于《錄鬼簿》。但編寫話本的只見陸顯之《好兒趙正》一例。“腹笥有文史”的朱桂英女士,講的是“道君艮岳及秦太師事”,則是講史家(見楊維禎《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但有無話本留傳,亦未可知。現存的《宣和遺事》則是收集了許多史料的一部話本,編者掌握不少史傳和詩詞的資源,文化修養較深,應該說是當時的“才人”。但《宣和遺事》可能并未全部付諸場上演說。我認為這也是話本的一種類型。因此我提出了講史平話的多樣性問題,對古代作品不能用一個標準來衡量,但從歷史發展的視角看,有些藝術性不強的本子,卻有很重要的史料價值和文獻意義,如《宣和遺事》就是。
清代的話本如《清風閘》《飛跎子傳》也是藝人自己整理的,但比較簡略,又沒有才人幫他潤色。俞樾雖然對《三俠五義》作了一點修改,但沒有仔細加工,所以沒能像《水滸傳》那樣成為杰作。
蘇州評彈是國家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也有許多世代累積型的話本和多種流派的唱腔。我作為蘇州評彈的老聽客,很關心它的保護和傳承。在探討近體詩的格律及吟誦問題時,覺得蘇州評彈在雅化和格律化的過程中,曾深受近體詩的影響,特別是以馬如飛為代表的《珍珠塔》和馬調系統的唱腔,最能體現傳統的吟誦方法。因此寫了《蘇州評彈與格律詩的吟誦》等文章,希望能以吟誦的方式來擴展傳統詩詞的傳承,包括對詩詞格律的普及。另一方面,也希望蘇州評彈的藝人,能繼承并發展前人的經驗,適當借鑒傳統詩詞的格律,提高評彈的藝術性。反過來,吟誦家也可以借鑒曲藝家的唱腔,適當改進吟誦的音樂性。例如平起式的七言詩,如果結句是“平平仄仄仄平平”的,在蘇州評彈里一般都是在第六字上延長行腔,而在第七字時卻很快收束,與其他劇種大多在末字上延長行腔迥然不同。我覺得近體詩的吟誦,也可以適當夸張第六字的長音,顯示“二四六分明”的平仄反差。最近在電視上聽到上海陸錦花女士指導、培養的小學生,用蘇州評彈唱腔吟唱的唐詩,比較準確地體現了平長仄短的聲調,也很好地給少年兒童傳播了古典詩歌和非物質文化遺產,這是一個一舉兩得的詩教方式,值得重視和提倡。
“常州吟誦”已被批準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以趙元任先生的吟詩方法為代表的。在目前百花齊放的吟誦流派中,我認為“常州吟誦”可以代表吳語地區及大多數方言地區的傳統吟誦方法,以“平長仄短”的聲調和兩字節、三字尾為基本節奏,是和近體詩的格律相適應的,完全可以作為“非遺”保護并傳承下去。其他流派的吟誦,是否分別列入“非遺”,還有研究討論的必要。至于以音階高低為藝術手段的歌唱方法則是在探討和試驗中的創新,同樣可以為傳統詩詞的傳播作出貢獻。
(作者單位:中華書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