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干《再唱一首山水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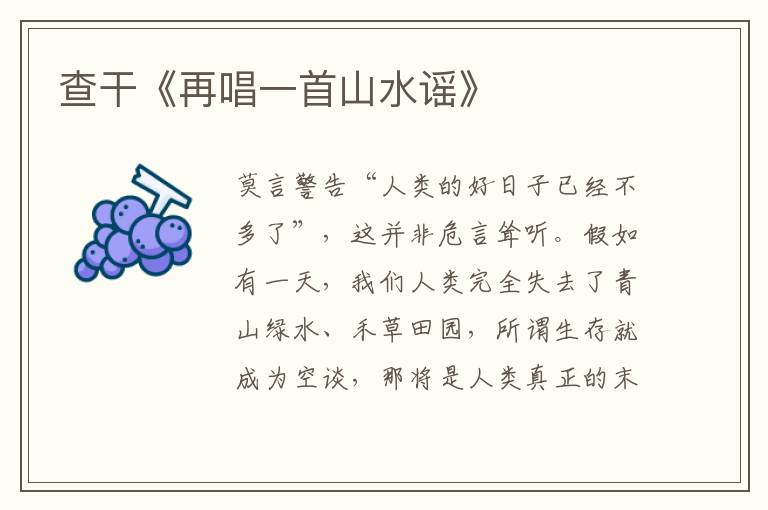
莫言警告“人類的好日子已經(jīng)不多了”,這并非危言聳聽。假如有一天,我們?nèi)祟愅耆チ饲嗌骄G水、禾草田園,所謂生存就成為空談,那將是人類真正的末日。
在農(nóng)耕文明時代,人們對青山綠水是崇敬、維護(hù)的。因為那時的人依山傍水,才得以生存。敬畏山水,依賴山水,是自然而然的事。而進(jìn)入工業(yè)文明之后,對于大自然而言,是災(zāi)難性的。山山水水滿目瘡痍,樹木花草、飛禽走獸日漸消失。為此,聯(lián)合國將每年的6月5日定為“世界環(huán)境日”,向世人敲響了警鐘。
而在古代中國,山水詩盛行是人所皆知的文化現(xiàn)象。說明我們的古人,對于自然環(huán)境的珍愛與重視程度有多么厚重。而今,則正好與之相反。有一年,我去登岳陽樓,見眼前的洞庭之水,浩渺之勢大為減色,甚至有些萎靡,令我不禁發(fā)出一聲浩嘆。曾經(jīng)有過一副古聯(lián):“八百里洞庭憑岳陽壯闊,兩千年赤壁覽黃鶴風(fēng)流。”在古人筆下,山與水是何等浩闊壯麗?而如今,人們對湖水的侵害和過度利用顯而易見,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警覺。“洞庭天下水,岳陽天下樓”,已非往日盛況是實事。至此猛然想起唐人劉禹錫的《望洞庭》一詩來:“湖光秋月兩相和,潭面無風(fēng)鏡未磨。遙望洞庭山水翠,白銀盤里一青螺。”那時的洞庭,月光水色互為交融,湖面浪靜風(fēng)平,如同未磨拭的銅鏡一般。遠(yuǎn)遠(yuǎn)望去,山水蒼翠如墨,好似潔白銀盤里托著一只青青的螺。青螺,指湖中的君山島。而今,別說水勢之微弱混濁,連水鳥都哀鳴有加,待在遠(yuǎn)岸,不肯靠近。在它們眼里,人已是異類。
想要改變這種孤家寡人的處境,人類需要與萬物和諧共處,去行善德、仁德,要去學(xué)習(xí)存世之道。師者,德之大也。那么,師到哪里去拜呢?師,又是誰呢?說來也簡單,在人的一生中,有很多選擇的機(jī)會,人,可以是師;物,也可以是師;山與水,更是。
子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意思是說:“智慧的人樂于像流水一樣,閱盡世間萬物,悠然、淡泊。仁義的人樂于像山一樣,巋然矗立,崇高、安寧。”孔子認(rèn)為,人和自然是一體的。山和水的特質(zhì),也反映到人的素質(zhì)中來,此言極是。一方山水,培育一方人的例子,從不鮮見。孔子不愧為圣者,在2500多年以前就道出人與自然的辯證關(guān)系。從傳統(tǒng)意義上講,我們的古人都是敬畏山水的。不像現(xiàn)代人,動不動就口出狂言——山高人為峰。不錯,現(xiàn)代人類的確掌握了一些科學(xué)技術(shù),掌握了某些支配自然的能力,為此,就把自己置于自然之上,顯得既淺薄又幼稚。
其實,在自然萬物中,人是最羸弱的一種。就生存能力而言,連螞蟻都勝于人類。人類憑的是可以動動腦筋,憑借外力來彌補自己的不足。機(jī)械,就是其中的一項。我常在蟻群出沒的洞口觀察它們?yōu)樯姹甲叩拿β瞪碛埃瑸樗鼈兛梢酝献弑茸陨泶髱妆兜奈矬w而感慨不已。不僅動物,連植物的生存能力也明顯優(yōu)于人類。舉例有二。一是30多年前,我第一次去登黃山,看見那些劈石而生的懸崖巨松,昂然向天,久經(jīng)風(fēng)雨而不倒時,靈魂受到了極大的震撼。顯然,那些松子是被風(fēng)吹到了絕處而后艱難地去發(fā)芽、扎根,終于尋出了一線生機(jī),并蓬勃存世。二是晨起我在河邊散步,見滿天柳絮在空中飄飄又搖搖地飛行,在尋找落生之地。不知為什么,一股悲憐之情油然生于心。它們生而離母是為尋找未來的生存之地,不僅順乎常理,更讓人動容。別看它們生得懦弱,骨子里卻是鏗然有聲的。它們以弱勝強(qiáng),最終成為參天大樹,那是怎樣的一種歷練過程?
值得心生敬畏和學(xué)習(xí)的,更有山與水。有人認(rèn)為,山與水只是自然之物,沒什么可考究和效仿的。此言差矣。首先說山,人類科學(xué)說它只是地殼運動中所隆起的一些高地。此說從淺層意義來講,當(dāng)然是對的。然而,地殼又因何而隆起?地球板塊兒又是由誰來裁定的?為何漂移?為何相擠?我們的研究還沒有深入到令人信服的程度,我們所看到的或許只是表層,而非實質(zhì)。我的故鄉(xiāng)是在群山環(huán)繞中的一處盆地,睜眼是山,閉眼也是山。因為有山,我們從小就不缺乏安全感。我在童年時就感到,故鄉(xiāng)的山不是一個死寂物,而是有靈有魂的生命個體。故鄉(xiāng)人那種不怕艱難困苦的堅毅性格,一定是由山的神教潛移默化而來的。山的屹立就是表率,山的蒼茫就是胸懷,甚至山的孤傲也感染著我們的一言一行。它像是智慧長老,也像是勤勉祖輩。“靠山”一詞的出現(xiàn)絕非偶然,山無言地教會我們站立,并挺起腰桿,甚至教會我們享受孤獨。山是不會相互撕斗、碰撞,相互欺凌和掠奪的,山所堅持的只是扼守崗位,堅貞不渝。山更不會以大欺小。珠穆朗瑪峰為眾山之首,然從未頭戴金冠,斥責(zé)眾小,這便是山的品格。竊以為,這是對一切生存哲學(xué)的最高詮釋。
而水,又何嘗不是?它是生命之液,唯有它可拯救一切生靈。有關(guān)水,我們的古代哲圣老子、孔子都有過深邃的解讀,“上善若水”之說就是一例。中華大地上的大江大河我見過無數(shù),它們是大地母親的動脈,流到哪里哪里就有生命的奇跡出現(xiàn)。而我對水的認(rèn)知是從故鄉(xiāng)的一條小河開始的。它是一條弱水,卻可以鋸石而千里流動。看似單薄的水流,居然可以把石頭磨成圓形,讓其隨流而滾,這使我驚嘆不已。水與山同,也從不相互排斥、抵擋、推搡,合流奔騰是它一貫的風(fēng)格。在我們故鄉(xiāng)人的性格里,都含有那條小河隨和柔情的基因。水可以包容一切,也滋養(yǎng)一切。水最具佛性,也最具母性。
至此,我終于明白,人為什么總是心懷鄉(xiāng)愁,并葉落歸根,因為,故鄉(xiāng)擁有這般值得推崇和效仿的山與水。更何況,它們教會我們的何止是堅毅和利他,更有扼守和仁愛。這一切,都是在潛移默化中流入我們血液里的,它也使我們的魂魄趨于安靜和純粹。對此,我們沒有理由不去感恩山與水,沒有理由不去點燃一炷心香,并以虔誠之心道聲:萬謝!假如我們心中,還有良知的話。
(此文刊發(fā)于《綠葉》雜志2020年第10期)
作者簡介
查干,中國作協(xié)會員,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研究會會員,中國詩歌學(xué)會理事,原《民族文學(xué)》 雜志編審。著有詩集《愛的哈達(dá)》《靈魂家園》等,另有散文、 散文詩、詩評散見于海內(nèi)外 華文報刊。作品被譯成英、 法、日、韓、匈牙利等文字介紹到國外。曾多次獲國家、省、 自治區(qū)文學(xué)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