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三《無名之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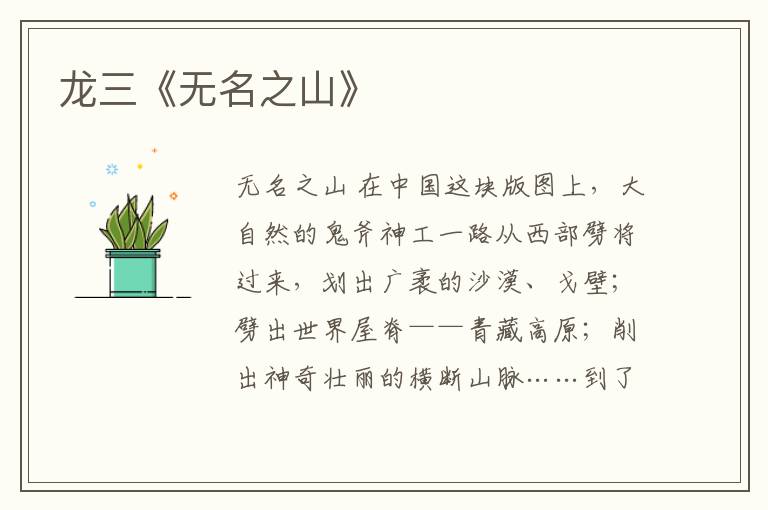
在中國這塊版圖上,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一路從西部劈將過來,劃出廣袤的沙漠、戈壁;劈出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削出神奇壯麗的橫斷山脈……到了云貴高原的邊城——宣威地盤,刀斧手累了,小歇了一會,出手就有些潦草:這里群山連綿,但沒有一座在地圖上被醒目地標出,更沒有一座在歷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這也不奇怪,云南遠離中原,自古就是蠻夷之地。中原的文明之光難以輻射到這里。
三山五岳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歷史記載詳盡而繁多,為之歌詠的人自然不計其數,天下名山大致如此。但也有一些很有特色的山,因為偏遠或是其他原因,一直無人問津,名不揚,景不顯。老東山就是這樣一座無名之山,但也有很多可圈可點之處。
老東山屬于烏蒙山系,地處云南高原向貴州高原傾斜的斜坡地帶,地勢較為平緩,有較齊的山峰線和較平緩的山頂面,是宣威最長的山脈。主峰滑石板海拔2868米,是宣威的最高峰。宣威人說起哪座山,常拿“高不過黎山,長不過東山”來類比。其實老東山既是最長的山,也是最高的山。
土著宣威人習慣稱呼老東山為石龍山。道光年間編修的《宣威州志》記載:“東山,一名石龍山,在城東七里。南北兩山蜿蜒相接,中抱小阜,圓如寶。郡人謂之寶山。下即安司舊宅,名河東營。東北之麓,亂石嶙峋,盤旋而上,夭矯如龍,石龍之名以此。”從主城區看過去,它就像一條縱貫南北的巨龍,頂上起起伏伏的山峰像龍鱗。從遠古到今天,它像一道長長的屏障橫臥在宣威城的東邊,靜靜地守護著宣威這座古老偏僻的小城,為古代宣威人民擋住了敵人的侵擾,擋住了寒風的侵襲,使宣威沒有遭遇過大動亂、大變革、大災荒。所以,石龍山在宣威人民心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石龍山龍頭伸到北邊的黃鶯硐、龍硐,龍尾直達南邊的高坡頂。兩山銜接處的寶山之下涌出一泉,當地人呼之“龍口”。幾年前,這里建了一座石廠,寶山被挖去一半,泉水也越來越小,幾乎要消失在本地的史志上了。有次我去登山,和一村民閑聊,他痛心地說:“這是石龍山的龍脈啊,無知的人,龍脈挖斷了,破了風水了呀”。
龍口上面有一堵懸崖,遠看像個風姿綽約的美人,名玉美人。關于玉美人,有兩種流傳比較廣的版本:一種說古代宣威境內有惡龍興風作浪,觀音大士就化身為一個彝族姑娘的模樣,在一處陡峭的懸崖邊和惡龍大戰,戰勝之后,她怕惡龍卷土重來,就把那堵懸崖變成那個姑娘的模樣,守護著宣威這塊壩子。另一種說法是:一個叫“玉美人”的美麗的彝族姑娘在給奴隸主家做工的時候,結識了主人家英俊勇敢的放羊娃。他們兩個互相傾慕,產生了至死不渝的愛情。一天,放羊娃外出放羊,突然,狂風大作,傾盆大雨隨之而來。羊群受到了驚嚇,四處逃竄。為了尋找丟失的羊羔,他墜落山崖不幸身亡。玉美人聽到這個噩耗之后就天天到那個山崖去哭泣,最后山崖就化為玉美人的模樣。為了紀念這段凄美的傳說,宣威市人民政府在向陽街和上堡街的十字路口塑了一個彝族少女的雕像,就稱為“玉美人”。為了紀念玉美人對宣威的保護,每年農歷的三月三日,宣威城可說萬人空巷,人們都去登山比賽,一直順小路爬到“玉美人”懸崖那里,上香、祭祀。“三月三,上東山”,這個日子逐漸演化成人們休閑、祈福、踏春、賽歌的習俗,所登的山也不再僅限于東山。
河東營背后的山坡上還有清末安土司的墓地。元朝為了籠絡邊疆,實行土官制,彝族首領安舉宗統一了宣威各部,成為統治宣威的第一代土司。從此安家世世代代世襲土司官位。山高皇帝遠,除了要給朝廷上貢,邊疆地區有高度自治,土司其實在本地相當于皇帝,權利至高無上。為了擴大自己的范圍,增強自己的勢力,土司之間經常發生戰爭,老百姓深受其苦。對朝廷,則態度強硬。至清代,云貴總督鄂爾泰看到土司制度的種種弊端,對不順從的土司采取強硬的政策,兵臨城下,進行毀滅性打擊,改派流官進行管理。那時,安家第二十二代土司安于蕃正以朝廷命官的身份忙著招兵買馬,擴充勢力以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鄂爾泰以毀壞官府形象的名義發兵進攻,活捉了安于蕃,安于蕃被革職解送江南的江寧府。自此,安家對宣威473年的統治結束了,一個王朝的身影遠去了。
安于蕃死后被運送回家鄉,當地人哀憐他,把他葬在他家宅院旁的上坡上。現在,安土司墓碑上的字跡已經模糊不清,依稀可辨出主人曾經顯貴的身份。荒草越長越高,快要淹沒墳頭了。此地沒有多余的墳墓,安家的其他人,大概在和鄂爾泰對抗的時候逃走了,或者全被殺了。這座孤墳,獨自守著曾經屬于安家的領地,顯得如此荒涼,讓人徒增傷感。
石龍山中段的半山腰有一座寺廟,名東山寺,又名松鶴寺,為明初所建。東山寺由活佛硐、普陀巖、祖師殿、靈光殿、大士閣、白齋洞、回廊、海會塔等主要建筑物構成,是儒釋道三教合一的佛教勝地。從山腳到寺前有一千零二十六級臺階,寺廟屢毀屢建,現存的松鶴寺重修于民國,門頭上的牌匾和對聯是民國時龍云所題。松鶴寺世代香火旺盛,出過不少名僧。
寺廟里柏樹森森,樹齡幾百年的比比皆是。寺內最古老的樹據考有1200歲了,是一棵古梅。這棵老樹在漫長的歷史時期度過了自己的花樣年華,為開出最美麗的花朵,她掏空了自己,盤虬的樹干上出現一個空洞,就像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五臟六腑都已經退化。古梅雖然沒死,但已經開不動花了。后來,人們用水泥封嚴那個洞穴,幾年前,古梅又煥發出新的生機,迎來了第二春,又年年盛開,甚至比以前還繁盛。每年大雪紛飛時,粉色的梅花和雪花交相輝映,紅色的院墻為背景,巨大的樹冠頂著千千萬萬朵梅花,那種美讓語言無法抵達。愛好攝影的人們為留下古梅的芳姿,把寺廟的門檻都踏破了。
老東山喀斯特地貌很明顯。這里有不為外人熟知的小石林,黑色的山石高高聳起,成林、成峰,山石上長滿青綠的灌木、荊棘、野草。它們艱難生存的狀態讓人動容,只憑石縫里有限的一點泥土,就能生出粗大的根系,盤根錯節,抓牢石塊,只為保住屬于自己那塊立足之地。那些泥土可能是大風吹來的,也可能是鳥兒銜來的。山里人家要在這石旮旯里討生活,其艱難程度可想而知。
山上有很多自然村,有些以姓氏命名的,比如朱彎,李家村。有些是彝族名稱,比如:卡基、謝且、色米依。也有些是鄉村常用名,如三家村、火石盆、芙蓉寨、馬場。東山上的土著民族是彝族,漢族多是明朝以后才有從江南遷來的。像西塔夸和色米依這樣的村子,一個村子只有幾家人,只有一所小學,一所小學只有十幾個學生和一個老師。這個老師是校長,還是全科老師、伙夫、校工。一般都是本地人,娶一個本地老婆,在一個學校里一呆就是一輩子。從小青年到退休,守著一代代孩子們,守著學校,守著大山,青絲熬成白發。本分、低調、受人尊敬。張家殺豬,李家宰羊,桌上總會給他留個位置。
西塔夸這個村,離城直線距離不遠,就在電廠背后的山坡上。在村里,可以看見電廠的大煙囪,可以看見城里錯綜復雜的電線網絡,可以看見城市的輝煌燈火。西塔夸人在黑暗里看了幾十年的燈火,村里的夜晚還是漆黑一片。沒辦法,村莊到山下幾乎是垂直的山坡,修路架線的艱難可想而知,直到2008年,西塔夸搭上了西部大開發的快車,終于架起了電線,點上了電燈,用上了電器,看上了電視。現在又趕上新農村建設,村里進城的公路也修起來了,不過是多轉幾個彎,多打幾個折,再陡的山坡,我們中國的面包車都能上去。
因為高寒,山頂除了課松樹(就是會結松子的樹)以外,就是大片大片的草地,山頂人家養殖和耕種并重。一般人家都有幾頭牛和一群羊。山上只能種植土豆、玉米、蕎麥等主糧,還有大藥(牛蒡)、大蒜、牛眼豆、蔓菁等經濟作物。
在我看來,東山的四季都是那樣迷人。
春天,各種品類的高山杜鵑次第開放,東山成了一座名副其實的花山。從山脊到山頂,從二月份開始,陸陸續續開到七月份。三、四月間開的紫色杜鵑最為壯觀,我們叫它碎米花。從電廠后面的山坡一直到最高峰滑石板,碎米花翻山越嶺,占領了半個東山,開成了花的海洋。多少世多少代,這些花只為牧羊人開放,而牧羊人看慣了這種景觀,并不覺得有什么特別之處。隨著徒步運動的興起(沒有徒步人到不了的山,沒有他們看不到的景),這大片大片、一坡一坡的花被驢友們發現了,他們又告訴更多的徒步人,東山就有了幾條經典的徒步路線,但殊途同歸,每條終點都指向滑石板。有了微信以后,驢友把圖片發到朋友圈,從此,東山這片花海就不再是牧羊人和驢友獨享了,大批大批的市民到來,賞花、拍照。忘形地尖叫、狂喊,甚至淚流滿面。你會發現面對驚心動魄的美,語言一點辦法都沒有,唯有回到蒙昧狀態,表現出一些不合常規的瘋狂之舉,才能夠把心中的感覺表現一二。
盛夏,大部分高山杜鵑才開放,潔白,純凈,大朵大朵的,牛乳中洗過一般。城里熱氣騰騰,山頂涼風習習,花香宜人。在青草上坐著、躺著、看蜂子在小花間采蜜,聽牛鈴在風中奏樂,跟牧民聊聊家畜的繁衍、糧食的收成,你會樂而忘返。傍晚,牧人還會熱情地邀你去他家做客。純正的火腿、各種山茅野菜、上好的包谷燒,傾盡所有,生怕有怠慢。
夏天還是各種山果成熟的季節,白破斑、野樹莓,烏榧,都好吃到停不下來。這些野果都太軟,容易腐敗,不好攜帶,所以,想吃就自己上山,吃夠再回來。還有栽秧果,紅彤彤的,煞是可愛,可是枝條上都是刺,摘的時候要十二分小心。這些野果最好端午前吃,端午過后就會生蟲子了。
端午節“游百病”,是宣威人的習俗,說是端午這天去山上游一游,就可消除百病,游百病的時候,順變采藥。老人們常說,端午這天,即使采回來一根草,都可做藥。有一年我們去“游百病”,在東段的山腰上發現有成片成片的面蒿花,黃澄澄,金燦燦,仿佛天空都成了金色。宣威人只在春天采嫩嫩的面蒿葉子做粑粑,滇西人習慣采花做粑粑。所以我們做的面蒿粑粑是綠色的,滇西人做出來的面蒿粑粑是金黃色的。面蒿葉子做出來的偏甜,面蒿花做出來的偏香。端午,山上的彝族青年男女還會上山對歌,把火辣直白的情歌唱給對眼的異性,如果對方中意,晚上就可帶回家見父母了。
農歷六月二十四,是彝族的火把節,也是彝族同胞們的狂歡節。從滑石板到小石林,從小石林到芙蓉寨,從芙蓉寨到安地,到處洋溢著節日的氣氛,殺羊、斗牛、祭祖、歌舞表演。來者都是客,不論漢族還是彝族,隨便走進哪一家,坐下就吃,大塊吃肉,大碗喝酒。吃飽喝足,黃昏以后,草地上燃起一堆堆篝火,歡快的彝族音樂響起,篝火舞會就開始了。不要害羞,手拉著手,幾圈下來,舞步熟了,人也就熟了。
即使是寒涼的秋季,東山也有各種不知名的小花,在自己那小塊領地熱烈地開放。金絲梅和野菊花是最尋常的兩種,它們都具有陽光的顏色,給大山增加一抹明艷的色彩。野菊花的藥用價值很高,每年都有很多人上山采摘,拿回來上蒸籠蒸,去除毒性和過多的寒性,然后放太陽底下曬干,收藏起來,著急上火、喉嚨疼痛、嗓子嘶啞的時候,抓出幾朵泡水,效果很好。
冬天,只要城里一下凌,山上必然就要結冰,那些枯枝亂草,被潔白的冰凌變成刀劍,變成羽毛,變成千奇百怪的形態。紅色的狗尿尿果被透明的冰包裹著,紅的更紅,白的更白,寒冰就有了三分暖意。最壯觀的是霧凇,霧凇是東山頂最尋常的景觀,宣威人根本不用跑到東北去看。
每年下凌或者下雪,我都要和朋友們結伴上東山,摔多少跤都阻止不了我們的腳步。去年,我們冒雪上山,一邊艱難地爬山,一邊大聲歌唱,雪太大,得隨時抖落身上的雪花,剛抖落一層,又積起一層。登到山頂,放眼一望,滿世界白茫茫一片。遇一伙人,撿來枯枝,燃起大火,燒洋芋,烤牛肉,喝大酒。看見我們,就邀我們過去同吃。之后,大家在冰天雪地里,圍著熊熊大火,跳起來了彝族的圓圈舞。讓人頓生一種山大王的豪情,恍惚覺得腳下廣袤的荒原“莫非王土”,天下眾多的賢士“莫非王臣”。
東山上到處藏著寶。春天,可以采各種山茅野菜,什么大藤菜、金剛藤、臭椿、棠棣花、苦刺花、大白花、蕨菜、木通藤、毛菜、毛菇……涼拌、清炒、紅燒,任由你折騰。城南有一家野菜館,一年到頭都可吃到野菜。老板夫婦兩個都是勤快人,春天采好多來,吃不完的晾干,其他季節備用。
夏秋兩季,幾陣日頭幾陣雨,漫山遍野是撿菌子的人,不論你在哪匹梁子、在哪個時段上山,大山都會給你留下一份。在林子里、草叢中,看見各種蘑菇頂開頭上的泥土,好奇地打量著這個陌生的世界。你伸出手來,帶著驚喜輕輕把它拾起來,它會鼓勵著你不斷地去尋覓這種驚喜。最開心的是撿到雞樅,撿到獨雞樅都很開心,更別說撿到一窩,幾朵乃至幾十朵,那種興奮一輩子都記得。我小時候就撿過一次雞樅,十幾朵,戴著黑色的尖頂帽子,擠擠挨挨在一塊包谷地頭,我拔豬草的時候猛然看見,高興得差點昏過去。
有兩種名貴的菌子,過去宣威人是不要的。一種是大花菌,一種是豬拱菌。大花菌有股藥味,人們嫌棄味道不好。不知從哪年開始,它突然有了一個文雅的名字——松茸,說是營養特別豐富,日本人尤其愛吃。名貴起來的大花菌,價格暴漲,人們才把它當寶貝,尋寶一樣上山去尋。豬拱菌原來也沒人吃,之所以叫這個名字,說是發情的母豬特別喜歡這種菌的味道。這是放豬人發現的,發情的母豬老是拱厚厚松針下的土層,拱出一個個黑黑的怪東西,格吧格吧吃下去,似乎就可以緩解荷爾蒙帶來的躁動。也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它有了個好聽的名字——松露,聽說在法國人那里,要幾千塊錢一斤。從此,人們舍不得放豬去拱了,都去自己刨來吃掉。宣威人吃松露和松茸都很奢侈,大盤上,蘸芥末吃,或者在火鍋里煮著吃。
東山上還有珍貴的藥材,比如草烏、燈盞花、連翹、柴禾、靈芝等。宣威人向來奉行藥食同源,很多草藥被當作美味佳肴來吃,比如春天吃的各種山茅野菜,好多就是中藥,像車前草、蒲公英、木通藤、苦刺花。瑞午節吃開胃的馬蹄香、滋補的小黑藥。冬天吃大草烏。大草烏是毒藥,一般用來泡酒外用,但宣威人本著以毒攻毒的原則,每年冬天必吃一兩回大草烏,可提高抵抗力,不感冒。煮大草烏有講究,得和火腿或臘肉一起煮,得煮七小時左右,中間不能斷火,不能加冷水。吃的時候可以喝酒,但不能喝冷飲,吃后就在家呆著,不能出去被冷風吹到。有人一次可以吃一碗。我嫌草烏太苦,難以下咽,最多能吃一兩個。
我父親生前經常到山里采藥,天晚了就尋個村莊住下,不需要認識,只要告訴人家你是干什么的,天晚了回不去了,需要投宿一晚,主人家就會熱情地招呼進去,還要提供一頓晚飯。在糧食最珍貴的年代,我家里也接受過天南海北的客人投宿:磨刀的、彈棉花的、補鍋的、賣丁丁糖的,我家人口眾多,只有一間房,客人來了,都是在樓板上打地鋪,在外流浪的人,也不嫌棄。可恨的是有一次住了兩個安徽人,半夜起來走了,把我家的半鍋飯連同銅吊鍋一起背走了,我媽難過了好長時間,爹說,都是天下的可憐人,如果吃得飽,誰會要你半鍋飯啊。我們都說,以后別讓生人住我們家了,可是下次有人來投宿,還是照樣收留,我也不知道,那些外地人怎么喜歡住我們家那又黑又破的老屋,它差不多是村里年代最久遠的房屋了。
山里還有珍貴的樹種,比如龍女花、云南松、杜仲、芙蓉、橡樹。謝且村有兩棵巨大的芙蓉樹,一棵開紅花,一棵開白花,是村里的圖騰物。村里人都什么重大的舉措,都要去樹下商量籌辦。有人要發毒誓,也要到這兩棵樹下發。
東山的幾種特產受到全市人民的喜愛。大藥,學名叫牛蒡,是滋補的藥膳。馬刺根,是清涼解毒的。都是秋后采挖。山上土地板結,要挖這些藥可不容易,力氣不足、臂力不夠的是挖不出來的。像我這種體單力薄的人,就不夢想自己挖了,總有人挖來街上賣。還有東山頂上的牛眼豆,開艷麗的花,每顆豆都有一只牛眼睛大。鄉村辦酒席,往往有這道菜,做法也簡單:煮熟、拌榶。洋芋、蘿卜、豬肉,都比其他地方的好吃。
在東山上行走,不經意就會走進一片墳塘,浦家墳塘、錢家墳塘、葉家墳塘、繆家墳塘……一個墳塘一個姓氏,他們生前都住在同一條街道,同一個村莊,死后在同一個墳塘,還是好鄰居,還可論輩分,仿佛只是換個地方換種方式繼續活。掐了墳地里的蕨菜,挖了墳地里的草藥,摘了墳地里的楊梅,撿了墳地里的菌子,道一聲叨擾,什么也不說,地下的村民也不會怪罪。
我的客廳和主臥正對著老東山,從我這里到山腳,直線距離只有七公里。從我24樓的窗口隔空看過去,只能看見它陡峭的坡度、暗黑的溝壑、荒涼冷硬的巖石、深色的植被和無數通往山頂的小路,再高再遠就是天空,天的無限也被它攔截了,變成一片想象的虛無。
對我來說,東山是智者,是知己。我第一次遭遇人生的不幸時,特別難過又無處訴說,我就想到它。我一個人騎著山地車,順著崎嶇的山路往上走,有幾處坡度實在太陡峭,我使出吃奶的力氣都蹬不動,不得不下來推著走,騎得精疲力盡才到達山頂。我把車子扔到一個山莊的圍墻外,穿過那片姜子樹林,一直往上爬,到達電視塔處,腳下就是懸崖,風猛烈地迎面吹來,有那么一刻,我真想飛身而下,一了百了,再也沒有人世的痛苦。但我又害怕萬一給途中的樹枝掛住,或者摔不死成殘廢(其實是還覺得生之可戀)。我慢慢從懸崖邊退回來,退回到林子里,陽光穿過樹林,斑斑駁駁地灑落下來,地上厚厚的枯枝敗葉被陽光烤的暖乎乎的,我躺下來,風也靜下來,只有樹葉和橡林子果在陽光里嗶嗶啵啵地響,那是它們的笑聲。風拂去我臉上的淚水,逐漸撤出林子的陽光催我回去了,我起身,抖掉身上的樹葉,也抖掉壞情緒。下山的時候,感覺身輕如燕,輪胎和地面摩擦的沙沙聲都那么有節律,聽了讓人熨帖舒暢。
以后遇到什么事,我就去找石龍山。來到山頂,在松林里走一走,在金黃的松針上躺一躺,山立刻就明白我肯定有不開心的事,它讓風送來一陣一陣的松濤,讓鳥兒為我唱支歌,讓草間那些螞蚱、蟈蟈給我跳舞。它讓牛兒遙起清脆的鈴鐺,讓小羊羔奶聲奶氣地叫喚……我知道它做這一切都是在告訴我要看得開,要學會放下。
石龍山不是什么名山,但在我心中,它是最靠的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