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片清風(fēng)薄霧里有痛更有愛(ài)》古耜散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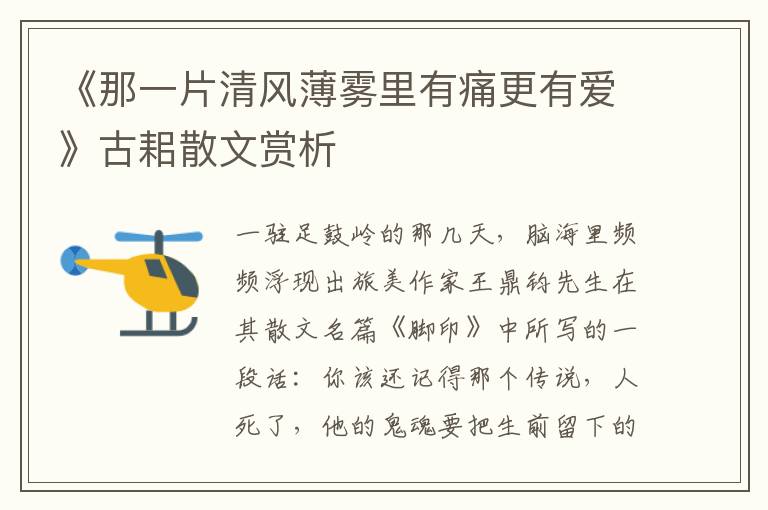
一
駐足鼓嶺的那幾天,腦海里頻頻浮現(xiàn)出旅美作家王鼎鈞先生在其散文名篇《腳印》中所寫(xiě)的一段話:
你該還記得那個(gè)傳說(shuō),人死了,他的鬼魂要把生前留下的腳印一個(gè)一個(gè)都撿起來(lái)。為了做這件事,他的鬼魂要把生平經(jīng)過(guò)的路再走一遍。車中船中,橋上路上,街頭巷尾,腳印永遠(yuǎn)不滅。縱然橋已坍了,船已沉了,路已翻修鋪上柏油,河岸已變成水壩,一旦鬼魂重到,他的腳印自會(huì)一個(gè)一個(gè)浮上來(lái)。
說(shuō)來(lái)也不奇怪,在鼓嶺這片如詩(shī)亦如畫(huà)的風(fēng)景里,最讓人賞心悅目,流連忘返的,固然是清風(fēng)里的柳杉,薄霧中的別墅——清風(fēng)、薄霧、柳杉、別墅,被稱為鼓嶺景區(qū)的四大看點(diǎn)——而最叫人浮想聯(lián)翩、思緒綿綿的,卻分明是在諸般風(fēng)景中一次次上演的“撿拾腳印”的故事——當(dāng)然,這故事不是虛幻的“傳說(shuō)”,而是確鑿的事實(shí);故事的主人公也不是戲說(shuō)中的“鬼魂”,而是一批批不遠(yuǎn)萬(wàn)里,前來(lái)中國(guó)尋蹤的金發(fā)碧眼的外國(guó)友人。
我相信,鼓嶺那彎曲的山道上和蔥綠的柳杉間,應(yīng)該留下了他們清晰的身影與足跡——
晚年定居美國(guó)洛杉磯的力瑪莉女士,因父輩就在中國(guó)而出生于民國(guó)初年的鼓嶺。長(zhǎng)大成人后,她執(zhí)教于福州城內(nèi)的華南女校。1940年,在日軍逼近福州的嚴(yán)峻形勢(shì)下,她和家人不得不撤離福州和中國(guó)。回到美國(guó)后,力瑪莉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給她的學(xué)生們寫(xiě)了一封發(fā)自內(nèi)心的致歉信:由于匆匆離校,有一節(jié)英語(yǔ)課未及上完。她希望早日返回中國(guó),為大家補(bǔ)上這節(jié)課。孰料此后國(guó)際風(fēng)云和個(gè)人境遇雙雙變幻,這一別竟是40年。1980年,乘著中國(guó)改革開(kāi)放的春風(fēng),華發(fā)滿頭的力瑪莉終于回到鼓嶺。在依舊留存的故居前,她想到的不僅是童年的歡快和青春的美好,同時(shí)還有傳播文化知識(shí)的夙愿。為此,她情愿拋下舒適的生活和繞膝的孫兒,于1984年再度來(lái)到福州,進(jìn)入剛剛恢復(fù)的華南女子學(xué)院,講授公共英語(yǔ),從事義務(wù)教育,直到一年期滿。
美國(guó)教會(huì)福州基督教協(xié)和醫(yī)院院長(zhǎng)蒲天壽和他的母親,早年曾在鼓嶺度過(guò)夏天。1984年,蒲天壽的女兒Betty率領(lǐng)整個(gè)家族重游鼓嶺,以紀(jì)念祖母蒲星氏來(lái)華一百周年;2010年底,Betty同丈夫、兩個(gè)女兒及女婿和孫子,再次來(lái)到鼓嶺,尋訪前輩的蹤跡和記憶,續(xù)寫(xiě)中美兩國(guó)的民間友情。
密爾頓·加德納先生是美國(guó)加州大學(xué)物理學(xué)教授,他1901年隨父母來(lái)到中國(guó),在福州度過(guò)快樂(lè)的童年時(shí)光,而夏天到鼓嶺度假的情景,尤其使他難忘。1911年,他隨全家返回美國(guó)。在此后的幾十年里,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回到兒時(shí)的中國(guó)和鼓嶺看一看。令人惋惜的是,由于種種原因,加德納先生未能如愿,彌留之際,他不斷喃喃自語(yǔ):“kuling,kuling”以表達(dá)難忘的牽念。加德納夫人不知道丈夫所說(shuō)的“kuling”在什么地方,為了實(shí)現(xiàn)丈夫的心愿,她多次到中國(guó)尋訪,但都無(wú)果而返。后來(lái),她在整理丈夫的遺物時(shí),意外發(fā)現(xiàn)了兩套郵戳完整的晚清時(shí)的中國(guó)郵票,經(jīng)一位中國(guó)留美學(xué)生幫助辨識(shí),終于確定加德納先生念念不忘的地方,就是福州的鼓嶺。當(dāng)時(shí),加德納太太激動(dòng)得手舞足蹈。時(shí)任中共福州市委書(shū)記的習(xí)近平,從報(bào)端獲知了這件事。他為美國(guó)人民的中國(guó)情結(jié)所感動(dòng)。于是,當(dāng)即決定邀請(qǐng)加德納夫人訪問(wèn)福州和鼓嶺。1992年8月,加德納夫人應(yīng)邀前來(lái),習(xí)近平不僅熱情接見(jiàn),而且安排她到鼓嶺游覽訪問(wèn)。當(dāng)天有9位年屆90高齡的加德納兒時(shí)的玩伴,同加德納夫人圍坐在一起暢談往事,追述舊景,令遠(yuǎn)道而來(lái)的客人欣喜不已。2012年2月,已是中國(guó)國(guó)家副主席的習(xí)近平應(yīng)邀訪美。在向友好團(tuán)體發(fā)表演講時(shí),他講了加德納夫婦與鼓嶺的故事。這個(gè)感人至深的故事不僅展現(xiàn)了中美兩國(guó)人民深厚的傳統(tǒng)友誼,而且把世界的目光又一次吸引到福州鼓嶺。
從這以后,有更多的外國(guó)朋友遠(yuǎn)涉重洋,前來(lái)鼓嶺尋蹤覓跡,撿拾前輩的腳印。他們當(dāng)中有終生想念中國(guó)的加德納先生的侄孫加里·加德納和李·加德納兄弟;有當(dāng)年第一個(gè)在鼓嶺建起西式別墅的英國(guó)人托馬斯·任尼的后人莎莉·安·帕克斯女士;有華南女子文理學(xué)院創(chuàng)辦人程呂底亞的后代、來(lái)自夏威夷的戈登·特林布先生……就在筆者采風(fēng)鼓嶺的同時(shí),又有一位研究鼓嶺文化的美國(guó)學(xué)者穆言靈女士前來(lái)尋蹤結(jié)緣——她的公公穆靄仁曾是陳納德將軍麾下飛虎隊(duì)的成員,抗戰(zhàn)結(jié)束后,執(zhí)教于福州協(xié)和大學(xué);她的丈夫穆彼得生在福州,兩個(gè)月時(shí),曾和家人一起在鼓嶺度過(guò)了一個(gè)夏天。而穆靄仁一家在鼓嶺的住所,正好是加德納一家返美時(shí)轉(zhuǎn)賣他人的房子,即加德納故居。這種特殊的因緣巧合使得穆言靈對(duì)鼓嶺別有一種深情。在共進(jìn)午餐時(shí),她激動(dòng)地告訴我們:“這里的風(fēng)景太迷人了,我太愛(ài)這個(gè)地方了。”“不久以后,我會(huì)帶著全家來(lái)看故居,這里有我向往的一切!”她還表示:“明年春天,我準(zhǔn)備帶一些外國(guó)孩子來(lái)這里,搞一個(gè)紀(jì)錄片,傳播綠色的東西。”可以相信,隨著時(shí)光的遷流,像穆言靈這樣熱愛(ài)鼓嶺,愿意傳播鼓嶺文化的國(guó)際友人會(huì)越來(lái)越多。
二
今天的鼓嶺大地,回蕩著外國(guó)友人留下的誠(chéng)摯而熱烈的贊美。每當(dāng)讀到或聽(tīng)到這些,我和土生土長(zhǎng)的鼓嶺人一樣,心中自會(huì)蒸騰起欣悅乃至自豪之情。只是這美好的情愫里,又總是摻雜著某些異質(zhì)的、矛盾的、一時(shí)難以說(shuō)清的東西。它仿佛在提示我:腳下的鼓嶺,并非一向晴川歷歷,鳥(niǎo)語(yǔ)花香。在中國(guó)近代史的縱深處,它原本飽含著難以消解的疼痛與哀傷——
1842年,鴉片戰(zhàn)爭(zhēng)失敗,清政府被迫與英方簽訂《南京條約》,開(kāi)放沿海五個(gè)通商口岸,福州正是被開(kāi)放的“五口”之一。從那時(shí)起,福州地面上,開(kāi)始有了“洋人”的蹤影。后來(lái),隨著以茶葉為主的中外商貿(mào)的不斷發(fā)展,更多的“洋人”抵達(dá)福州,到1866年,至少有17個(gè)國(guó)家在福州建立了領(lǐng)事館。
1884年,馬江之戰(zhàn)爆發(fā),福建水師遭受法軍重創(chuàng),清廷船政事業(yè)由此一蹶不振。而列強(qiáng)勢(shì)力則如日中天,一時(shí)間,數(shù)不清的西方外交官、牧師、商人、醫(yī)生和教授云集福州。
1886年,英國(guó)駐馬尾領(lǐng)事館醫(yī)生托馬斯·任尼在鼓嶺建起第一座夏日別墅。此后,陸續(xù)有英國(guó)、法國(guó)、美國(guó)、日本、俄國(guó)、德國(guó)、西班牙、墨西哥等20多個(gè)國(guó)家的外交官和僑民到鼓嶺避暑納涼,并興建別墅。據(jù)資料統(tǒng)計(jì),截止二十世紀(jì)三四十年代,鼓嶺上的洋人別墅在鼎盛期曾達(dá)300多座,夏日住在別墅避暑的外國(guó)人數(shù)以千計(jì)。
時(shí)至今日,對(duì)于上述歷史,已有學(xué)界達(dá)人試圖作別開(kāi)生面的詮釋,然而在我看來(lái),不管學(xué)者的理論如何新潮,思路怎樣巧妙,這段歷史本身所承載的闖入者的強(qiáng)悍與驕橫以及本民族的屈辱和劫難,仍然是無(wú)法改變的基本事實(shí),也是我們今天認(rèn)識(shí)和評(píng)價(jià)那段歷史的重要前提。正因?yàn)槌钟羞@樣的執(zhí)念,我在觀覽洋鏡頭留下的鼓嶺影像時(shí),腦海里便多了一份敏感、疑惑和警醒:
——盛裝華服的外國(guó)女士和先生們?nèi)宄扇海虼扒熬蹟ⅲ驊敉饧{涼,或山坡眺望。他們?cè)谝黄鹫f(shuō)些什么不得而知,只是那舒展、愜意且略帶驕矜的神情,總讓人想起堅(jiān)船利炮的作用。
——一個(gè)洋人家庭出行,幾位轎夫和挑夫在一旁伺候。這在當(dāng)年的鼓嶺應(yīng)該是司空見(jiàn)慣的場(chǎng)景。然而,這司空見(jiàn)慣的場(chǎng)景偏偏隱藏著鼓嶺勞動(dòng)者習(xí)以為常的艱難生存。請(qǐng)看曾當(dāng)過(guò)轎夫的王英思的回憶:“那時(shí)候,我才三十來(lái)歲,一到夏天就要去當(dāng)轎夫。下半夜扛篼跌跌撞撞下山,在抬上外國(guó)人和他們豢養(yǎng)的叭兒狗、狼犬后,趕在午前回來(lái)。下山上嶺有4000多層石階。”(《鼓嶺史話》)內(nèi)中的悲苦與無(wú)奈,早已超出了今人的體驗(yàn)和想象。
——原住鼓嶺的中國(guó)鄉(xiāng)民也被收入外國(guó)人的鏡頭:七位裹了小腳的婦女橫坐一排;十幾位頭上留了辮子的男子手持折扇,分三排而坐,據(jù)說(shuō)是日間在鼓嶺上課的學(xué)生;十一位鄉(xiāng)民中有七八位赤裸了上身,他們?cè)诘桶婆f的農(nóng)舍前或坐或立,大約是勞作間的小憩……我們沒(méi)有理由挑剔這些生活場(chǎng)景本身的客觀性與真實(shí)性,只是這樣的客觀與真實(shí),是否也有意或無(wú)意地滲入了拍攝者特有的、當(dāng)年曾被魯迅所抨擊的“到中國(guó)看辮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麗看笠子”的觀賞樂(lè)趣和獵奇心理呢?
面對(duì)如此的歷史鏡像,我還是感到了苦澀和沉重。
三
讓人稍覺(jué)寬慰的是,從目前能夠找到的材料看,當(dāng)年的鼓嶺之上,最終保持了大致的平穩(wěn)與安寧,有些時(shí)候,有些場(chǎng)合,甚至洋溢著和諧、歡快與融洽。不是嗎?鼓嶺郵局(1902年6月16日開(kāi)辦)門外不遠(yuǎn)處,有一口水井,上面刻有“外國(guó)、本地公眾水井”的字樣,不管這樣的說(shuō)明出自何人,有何背景,它所傳遞的基本信息與當(dāng)年口岸城市外國(guó)租界普遍存在的華人歧視,分明截然相反。今天的鼓嶺老街上,外國(guó)人修建的游泳池依舊保存完好。據(jù)說(shuō),它最初照搬西方文明,是男女共用的,但聽(tīng)到當(dāng)?shù)厝怂^“有傷風(fēng)化”的議論后,便改為男女分用,游泳池也由一個(gè)變成了四個(gè)。這當(dāng)中無(wú)疑包含了外國(guó)人對(duì)中國(guó)國(guó)情和風(fēng)俗的理解與尊重。在鼓嶺文化發(fā)展與旅游論壇上,穆言靈女士向大家提供了一張照片:一個(gè)風(fēng)度翩翩的美國(guó)男子手里提著一只雞,正喜氣洋洋地走在鼓嶺的山道上。據(jù)穆女士介紹,這位男子就是她的公公穆靄仁,當(dāng)年他給一個(gè)受重傷中國(guó)人輸了血,中國(guó)人便以雞相贈(zèng),作為回報(bào)。這個(gè)鏡頭是珍貴的,也是感人的,它足以讓人想起“愛(ài)心無(wú)國(guó)界,人間有真情”的說(shuō)法。諸如此類體現(xiàn)了中外民間友情的事例,在舊日鼓嶺上還可找到若干:外國(guó)人開(kāi)辦的學(xué)校可以免費(fèi)讓中國(guó)人前來(lái)就讀;外國(guó)人修建的網(wǎng)球場(chǎng)并不拒絕中國(guó)人參與;外國(guó)人舉行的生日宴會(huì)竟然也邀請(qǐng)其中國(guó)鄰居……
在西方列強(qiáng)挾炮艦撞開(kāi)天朝國(guó)門的嚴(yán)峻背景下,鼓嶺之上何以會(huì)有這一幕幕的友善、和睦,其樂(lè)融融?要厘清此中原委,我們不能不承認(rèn)當(dāng)年鼓嶺的情況存在某種特殊性。
羅素曾把西方人到中國(guó)來(lái)的目的概括為:打仗、賺錢和傳教。作為對(duì)晚清西方人在華行為的一種整體描述,這堪稱準(zhǔn)確而精到;只是具體到此間登上鼓嶺的外國(guó)人來(lái)說(shuō),情況卻發(fā)生了明顯變化:離開(kāi)炮火連天的戰(zhàn)場(chǎng),打仗已是無(wú)從談起;置身綠水青山之間,賺錢的欲望也已階段性消歇,取而代之的是充分的休閑和盡情的娛樂(lè);傳教的熱情倒是漸趨高漲,清脆的鐘聲伴隨著悠揚(yáng)的詩(shī)唱,成了鼓嶺上空特異的聲響。而無(wú)論休閑還是傳教,都需要盡可能協(xié)調(diào)友善的人際關(guān)系,也都會(huì)很自然地派生出寬松的氛圍與平和的情調(diào)。更何況“愛(ài)”是基督教思想的內(nèi)核,以人的善行來(lái)表達(dá)神的愛(ài)心,正是基督教教義在中國(guó)傳播的重要方式。
至于原住鼓嶺的中國(guó)鄉(xiāng)民,一向生活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經(jīng)濟(jì)之中,耕讀齊家,積累財(cái)富,應(yīng)當(dāng)是他們最強(qiáng)烈也最穩(wěn)定的愿望。大批外國(guó)人登嶺,并沒(méi)有破壞原有的一切,相反還帶來(lái)了新的社會(huì)景觀和生活內(nèi)容,特別是帶來(lái)了中國(guó)大地上最初的勞動(dòng)力市場(chǎng)和商品經(jīng)濟(jì)。面對(duì)驟然出現(xiàn)的生財(cái)乃至生存之道,他們顯然沒(méi)有理由不做出欣喜而積極的回應(yīng)。
四
百年鼓嶺有愛(ài)也有痛,有歌也有哭。當(dāng)這一切以“復(fù)調(diào)”形態(tài)匯入歷史長(zhǎng)河時(shí),有一個(gè)問(wèn)題顯然值得我們深入探究:當(dāng)年許許多多的外國(guó)人為什么喜歡鼓嶺,難忘鼓嶺?
最有資格回答這一問(wèn)題的,無(wú)疑是那些披蒙著歲月煙塵,一次次登上鼓嶺,并在那里度夏的“老外”們。事實(shí)上,他們當(dāng)中的不少人確曾將自己在鼓嶺的見(jiàn)聞與感受,寫(xiě)進(jìn)文章、書(shū)信或日記。遺憾的是,這些文字的絕大部分,迄今仍靜躺在不同國(guó)家的圖書(shū)館里,只有吉光片羽有幸化身中文,進(jìn)入中國(guó)讀者的視線。惟其如此,我們今天梳理“他者”眼中的鼓嶺之戀,只能在盡量占有第一手材料的基礎(chǔ)上,作以“我”為主的綜合分析。
毫無(wú)疑問(wèn),鼓嶺之所以獲得外國(guó)人的關(guān)注和向往,首先是因?yàn)樗堑锰飒?dú)厚的自然與氣候條件。“鼓嶺位于鼓山之巔,仿佛寶塔之尖頂,登峰四望,可以極目千里,看得見(jiàn)福州的城市民房櫛比,及兇濤駭浪的碧海,還有隱約于紫霧白云中的巖洞迷離,峰巒重疊。”這是現(xiàn)代女作家廬隱眼中的鼓嶺,它以居高臨下的視角,勾勒出鼓嶺特有的形勝之美。而鼓嶺之美以夏天為最。對(duì)此,熱愛(ài)旅游的郁達(dá)夫有過(guò)準(zhǔn)確介紹:“因東南面海,西北凌空之故,一天到晚,風(fēng)吹不會(huì)停歇……城里自中午十二時(shí)起,到下午四點(diǎn)中間,也許會(huì)熱到百度,但在嶺上,卻長(zhǎng)夏沒(méi)有上九十度的時(shí)候。”(這里的氣溫度數(shù)當(dāng)是華氏標(biāo)準(zhǔn)——引者注)1885年炎夏,因有急診須從福州趕往連江的美國(guó)教會(huì)醫(yī)生伍丁,在抄近路翻越鼓嶺時(shí),意外地發(fā)現(xiàn),較之城內(nèi)的溽熱難耐,這里竟然涼風(fēng)習(xí)習(xí),清爽宜人。于是,他將這一消息廣而告之,鼓嶺很快成了外國(guó)人的避暑勝地。正如全國(guó)解放后最后一個(gè)離開(kāi)鼓嶺的麻安德牧師所言:“鼓嶺是我們夏天的香格里拉,我們?cè)谀抢锍藳觥⒎潘伞⒐ぷ鳌⒊瑁硎茉谝黄鸬目鞓?lè)。”亦如潘天壽的女兒Betty所回憶的:“鼓嶺的夏天很涼爽,有美麗的樹(shù)林和翠綠的梯田。因?yàn)槭寝r(nóng)村,生活節(jié)奏也非常慢。我們每年都盼望著夏天的時(shí)候到鼓嶺上去。”
當(dāng)然,鼓嶺之上,并非只有秀麗的風(fēng)景和清涼的氣候,除此之外,豐富的物產(chǎn)也是它的一大優(yōu)勢(shì)。其中作為農(nóng)特產(chǎn)品的甘薯、白蘿卜、合掌瓜、薤菜、小筍、蘑菇、土雞等等,更是憑借大自然的異樣恩賜,培養(yǎng)了許多人的味蕾與口福,同時(shí)扯起了他們的憶念和牽掛,這當(dāng)中理所當(dāng)然的包括上山避暑的外國(guó)人。美國(guó)人畢腓力在成稿于1895年的《鼓嶺及四周概況》中寫(xiě)道:每年五月端午之后到八月中秋之前,有許多做生意的中國(guó)人,會(huì)跟著避暑的外國(guó)人一起上山,在鼓嶺開(kāi)設(shè)店鋪,為他們提供生活必需品和其他服務(wù)。這時(shí),鼓嶺的農(nóng)特產(chǎn)品如番薯、蘿卜、合掌瓜、薤菜、螃蟹菜等,因?yàn)橥鈬?guó)人喜歡吃,所以成了中國(guó)生意人的主營(yíng)商品。而外國(guó)人喜歡鼓嶺農(nóng)特產(chǎn)和中國(guó)餐飲這一點(diǎn),在加德納夫人多年之后的講述中正好獲得了印證。她告訴我們:加德納先生在回國(guó)后的幾十年間,始終難忘兒時(shí)在鼓嶺的飲食習(xí)慣,他幾乎每天都要吃一餐中國(guó)飯,大米粥和白蘿卜成了他的最愛(ài)。
鼓嶺是東海之濱的避暑勝地,當(dāng)然也是中國(guó)大地的鄉(xiāng)土一隅。這使得外國(guó)人一旦登上鼓嶺避暑,也就開(kāi)始了同中國(guó)鄉(xiāng)村與鄉(xiāng)民的密切接觸。這時(shí),一種長(zhǎng)期存活于中國(guó)民間的淳樸、和諧、健朗的生活氛圍與人際關(guān)系,如同一幅生動(dòng)別致的畫(huà)卷,次第展現(xiàn)于外國(guó)人面前,必然會(huì)引發(fā)他們新奇的感受與豐富的想象。這里,我們不妨從廬隱、郁達(dá)夫記述上世紀(jì)二三十年代鼓嶺風(fēng)情的散文中,選擇兩個(gè)片段稍加管窺與推衍。
片段之一:來(lái)自廬隱的《房東》。1926年夏天,時(shí)在福州城內(nèi)教書(shū)的廬隱,來(lái)到鼓嶺避暑度假。一天晚飯后,“我”和房東坐在院子里話家常。女房東告訴“我”,晚上如果怕熱,就把門開(kāi)著睡。“我”驚訝地說(shuō):“那怪怕的,如果來(lái)個(gè)賊呢?”
“呵喲師姑!真真的不礙事,我們這里從來(lái)沒(méi)有過(guò)賊,我們往常洗了衣服,曬在院子里,有時(shí)被風(fēng)吹了掉在院子外頭,也從沒(méi)有人給拾走……”我聽(tīng)了那女房東的話,由不得稱贊道:“到底是你們村莊里的人樸厚,要是在城里頭,這么空落落的院子,誰(shuí)敢安心睡一夜呢?”那老房東很高興的道:“我們鄉(xiāng)戶人家,別的能力沒(méi)有,只講究個(gè)天良,并且我們一村都是一家人,誰(shuí)提起誰(shuí)來(lái)都是知道的,要是作了賊,這個(gè)地方還能住得下去嗎?”我不覺(jué)嘆了一聲,只恨我不作鄉(xiāng)下人……
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據(jù)說(shuō)是歷史上盛唐貞觀之治特有的社會(huì)景觀,然而,它在近現(xiàn)代的鼓嶺鄉(xiāng)間,卻成了由來(lái)如此,隨處可見(jiàn)的生活小景,是農(nóng)人們習(xí)以為常的道德約束。可以想象,當(dāng)滿載文化優(yōu)越感的“老外”們?cè)跓o(wú)意中獲知這些,內(nèi)心的驚訝和贊賞,恐怕要比廬隱來(lái)得更強(qiáng)烈。他們或許會(huì)聯(lián)想到發(fā)生在西方啟蒙時(shí)代的長(zhǎng)達(dá)百年的“中國(guó)崇拜”,進(jìn)而意識(shí)到,在中國(guó)民間,善良的人性與高尚的道德,始終光彩熠熠,綿延不絕。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喜愛(ài)和贊美鼓嶺,實(shí)在是再正常不過(guò)的事情。
片段之二:來(lái)自郁達(dá)夫的《閩游滴瀝之四》。1936年的清明節(jié),供職于福建省政府的郁達(dá)夫,同六位朋友一起登上鼓嶺,試圖租幾間小屋以度炎夏。“我”等正行走間,但見(jiàn):
在光天化日之下,嶺上的大道廣地里,擺上了十幾桌的魚(yú)肉海味的菜;將近中午,忽而從寂靜的高山空氣里,又傳來(lái)幾聲鑼響;我們正在驚疑,問(wèn)有“什么事情發(fā)生了么?”的中間,一位須發(fā)斑白的老者,卻前來(lái)拱手相迎,說(shuō)要我們?nèi)⒓映运麄兊那迕骶迫ァ>剖欠旁谘箬F的大煤油箱里,擱在四塊亂石高頭,底下就用了松枝樹(shù)葉,大規(guī)模地在煮的。跑上前去一看,酒的顏色,紅的來(lái)像桃花水汁……嘗了幾口之后,卻覺(jué)得這種以紅糟釀成的甜酒,真是世上無(wú)雙的鮮甘美酒,有香檳之味而無(wú)紹酒之烈;鄉(xiāng)下人的創(chuàng)造能力,畢竟要比城市的居民,高強(qiáng)數(shù)倍,到了這里,我倒真感得我們這些講衛(wèi)生、讀洋書(shū)的人的無(wú)用了。
在現(xiàn)存的關(guān)于鼓嶺的歷史影像中,可以看到中外人士在戶外坪地上共享家宴的熱鬧場(chǎng)景。以此類推,郁達(dá)夫們的“奇遇”應(yīng)該也曾經(jīng)出現(xiàn)在外國(guó)人身上。面對(duì)鼓嶺鄉(xiāng)民的熱情有禮,身臨其境的外國(guó)人做何感想,我們一時(shí)找不到直接的答案,但它讓我想起阿拉伯近代著名思想家謝基卜·阿爾斯蘭(Shakid Arslan)寫(xiě)于1902年的一段話:“普天之下,再無(wú)一邦如中國(guó)那樣尊崇習(xí)俗與禮節(jié),也再無(wú)一方人士如中國(guó)那樣響應(yīng)人道之教化。性格溫順,是中國(guó)人與生俱來(lái)的德行,無(wú)論老幼,都秉有這一德行。他們以兄弟互稱,有‘四海之內(nèi)皆兄弟’之說(shuō);同輩之誼,與兄弟之情無(wú)異。”在我看來(lái),這段“他者”之見(jiàn),很可以作為當(dāng)年鼓嶺情景的畫(huà)外音,它比較準(zhǔn)確地傳遞出中華民族倫理道德上的某些特點(diǎn)和魅力。而這些正可以構(gòu)成外國(guó)人喜愛(ài)、留戀和向往鼓嶺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