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枚“土豆”》李涵睿散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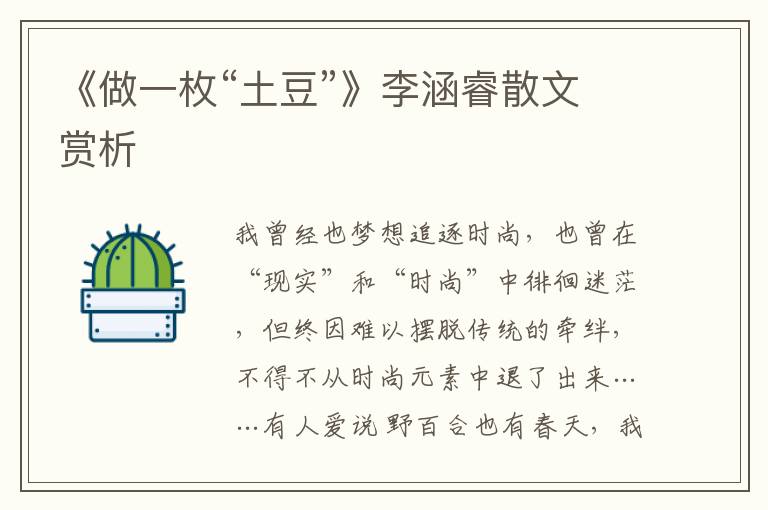
我曾經也夢想追逐時尚,也曾在“現實”和“時尚”中徘徊迷茫,但終因難以擺脫傳統的牽絆,不得不從時尚元素中退了出來……
有人愛說 野百合也有春天,我卻清楚知道:土豆長不成牡丹。土豆有它的宿命,土里土氣的表里注定它只能蝸居鄉村,不服氣就滿懷苦恨,終日仰面灰蒙蒙的天空;服氣了就風云散去,眼前一片平和的田園風光。我現在正有計劃實踐“土豆”生活,美其名曰“回歸傳統”。比如: 和朋友聯系手機少用、電郵不用、開始寫信,隨心縱馬,聊到哪算哪,字雖潦草卻發乎本心,滿紙真意和溫潤,這和不辨牛馬的電子版的“笑臉”、“大贊”不同,我心里想什么全在字里行間。用鋼筆在毛邊信紙上寫它幾百字,如同種了一畦蘭花,雖然不比鄭思肖的清幽雅麗,可暗香浮動,我想友人展開信紙時一定能會心一笑。欲寄彩箋和尺素,山長水闊又如何?
無緣時尚,就回歸傳統,出游只去海角天涯、老林朔漠、川藏的寂寞長路、山野的冷艷林泉,絕不再去趕集一般的勝地;居家就多翻翻書,和家人聊著長長的天兒迎來日出送走晚霞,讓手機休眠,讓牽著我們鼻子走的微信微博再也不能把我們玩弄于股掌之間——其實,我們玩它們的時候,更像是它們牽著我們遛。
我們處在一個迷失自我的時代。不是“粉兒”就是“控”,這如何是好?美國生產高端蘋果機的工程師們把子女送去硅谷的華德福學校,看中的是那里有一個規定: 學生七年級(大約十二三歲)前不允許接觸手機、電腦,這些東西有時候也是一種毒。美國人認為: 19世紀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大都能畫出一幅不錯的畫,那是自己的眼睛和心靈合作創作出的作品。如今,即使長春藤這樣的名校中,大學生會畫畫的也難尋覓,相機把大家對美的深層體驗掏空了。我們也一樣,如今的很多大學生連基本的生活都不能自理,心理上是個殘障人。
要想做一枚真誠的土豆并不容易,首先要認識自己,但“人,認識你自己”卻是最難的一件事。孫犁說魚翔淺底駝走大漠乃極致之美,就是因為這是大自然的固定法則。昨天讀了一則關于孫荃女士的短文《身邊的霍香》: 被“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的郁達夫拋棄后,孫女士安靜地在富陽生活,守著孩子和門口的霍香——她不抱怨生活薄情,心中和身上的霍香濃郁,幾十年間過得怡然自適——不抱怨生活,這就是生活得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下定了決心做“土豆”,心境忽然就平和了,如同越過盛夏、撲進金秋的懷抱。柔風軟陽讓堅硬的青澀情懷很快就變得微甜,就像被季節的金手指點化過的一個國光蘋果或天津鴨梨。不再張揚地高掛枝頭、搖曳清風,而是安靜地去庫房醞釀滋味,散發絲縷清香,帶來微紅的喜氣,讓看到蘋果的人感受到一些溫存氣息。
蒼茫夜色,細雨縹緲,翻開本《讀者》,心里平淡清靜,就如同小桌上那杯暖暖的清茶。做一枚“土豆”,真的沒有什么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