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叔河《時務學堂何處尋》隨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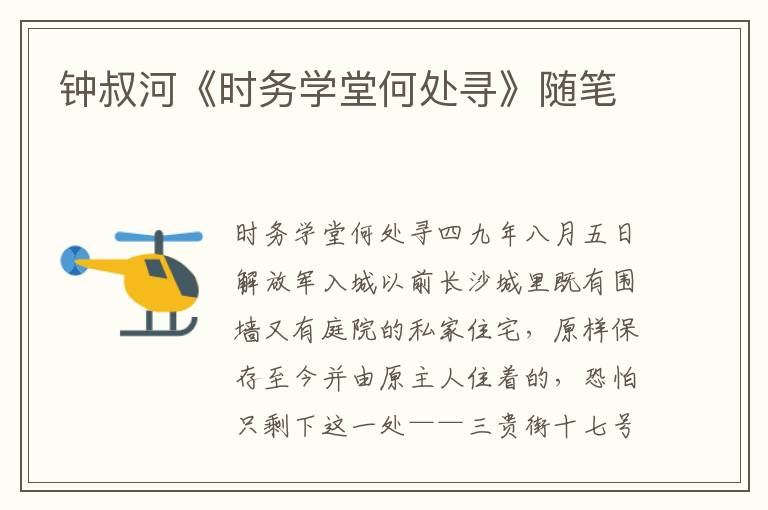
時務學堂何處尋
四九年八月五日解放軍入城以前長沙城里既有圍墻又有庭院的私家住宅,原樣保存至今并由原主人住著的,恐怕只剩下這一處——三貴街十七號陳宅了。
風雨蒼黃五十年,人和宅子能巋然至今,必有其不平常之處。第一是入須活得久,老先生今年已九十四歲;第二是還須有來頭,他抗戰(zhàn)前大學畢業(yè)后即“下海”經(jīng)營工商業(yè),不到四十歲便成了長沙市工業(yè)聯(lián)合會理事長,建國后當過全國政協(xié)委員,留下這棟私宅也是最高領導過問的結果;第三是房子建得好,而且還是“時務學堂故址”,有梁啟超的題字。
舊中國也曾嘗試走現(xiàn)代化道路,最像模像樣的一次,就是以“戊戌”為年代標志的清末維新變法運動。運動的思想領袖是康有為,其大弟子和助手即梁啟超(任公)。運動的中心在北京,惟一的“實驗省”卻是湖南。
湖南當時的撫臺陳寶箴,臬臺黃遵憲,學臺江標、徐仁鑄都是維新黨。他們推行的新政,重要的一項便是開辦時務學堂。這比京師大學堂(北大)的建校還早一年,比北洋大學堂(天津大學)則晚一年,但北洋只設理工科,這里卻以“時務”為名。梁啟超后來回憶道:
秉三(熊希齡)與陳、黃、徐諸公設時務學堂于長沙,而啟超與唐君紱丞(才常)等同承乏講席。……除上堂講授外,最主要者為令諸生作札記,師長則批答而指導之。發(fā)還札記時,師生相與坐論。時吾儕方醉心民權革命論,日夕以此相鼓吹……
這樣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顯示著人文的色彩,充滿了改革的精神,與只培養(yǎng)技術人材的理工科大學迥然不同。這是因為,辦學和執(zhí)教者除上述諸人外,還有陳三立(寶箴之子,任職吏部,此時在長沙助父)和譚嗣同,也都是積極主張維新變法的。在這些人的鼓吹教導下,短短時間內,便培養(yǎng)出了蔡艮寅(鍔)、范源濂(民國教育總長、北師大創(chuàng)辦者)、楊樹達(漢語學家、前中央研究院院士)等優(yōu)秀學生,在教育史上留下了燦爛的一頁。
先父昌言公(字佩箴)為時務學堂第二班外課(不在學堂寄宿)生,六十年前和我談及學堂的事時,猶神采飛動。蓋學堂實為湖南維新運動之中心,亦因此而受到了以岳麓書院為中心的守舊派“王葉二麻子”的猛烈攻擊。這種攻擊首先指向學堂的教法和教材,卻完全著眼于政治,采用的手段也完全是政治的。據(jù)梁氏好友狄平子的記載:
任公于丁酉冬月將往湖南任時務學堂時,與同人等商進行之宗旨:一漸進法,二急進法,三以立憲為本位,四以徹底改革,洞開民智,以種族革命為本位。當時,任公極力主張第二第四兩種宗旨。……其改定之課本,遂不無急進之語。于時王先謙葉德輝輩,乃以課本為叛逆之據(jù),謂時務學堂為革命造反之巢穴,力請于南皮(湖廣總督張之洞)。賴陳右銘中丞早已風聞,派人午夜告任公,囑速將課本改換。不然,不待戊戌政變,諸人已遭禍矣。
戊戌政變發(fā)生,譚嗣同、唐才常先后被殺,陳氏父子和江、徐均革職永不敘用,黃遵憲也被“放歸”。時務學堂則由舊派接管,改為湖南大學堂,校址也從此處遷往落星田了。
三貴街南出小東街(后拓修成中山西路),學堂故址在兩街交會處,系清朝大學士劉權之故宅。劉權之亦文化名人,《四庫全書》在事諸臣,正總裁皇六子、皇八子等,副總裁梁國治、劉墉等,總閱官德保等,都只掛名不做事。排名其后的總纂官、總校官和總目協(xié)勘官,才是實際的工作班子。總目協(xié)勘官負責各書校勘編輯,事最繁,任最重;劉權之為其首席,是《四庫全書》的“第一責任編輯”。
入民國后,劉氏后人衰敗。學堂遷走,這里賣給商家,成了“泰豫旅館”。一九二二年梁啟超來長沙講學,在這里留下了如下題記:
時務學堂故址
二十六年前講學處,民國壬戌八月重游泐記,梁啟超
現(xiàn)在的屋主人陳先生抗戰(zhàn)勝利后在長沙從事營造業(yè),買下“泰豫”這片地產,建樓成立“中原公司”,并在三貴街一側為自己蓋了這棟私宅。最使他得意的是,還以重金購得了這件梁啟超墨寶,后來并刻石立碑,嵌在院內北墻上。
四九年八月以后的事無法詳談,只說三點:(一)中原公司的樓早成了市糧食局用房,如今又成了職工宿舍;(二)題記原件已為湖南大學收藏,偏偏展示在戊戌時反對“時務”最力的岳麓書院里;(三)幾經(jīng)周折,屋主人對房屋的所有權終于得到了承認,遺憾的是“時務學堂故址”的地位卻一直“妾身未分明”,陳家“文革”中被抄走的兩大箱文物,最后被送到了省圖書館,至今也尚未歸還。
如今到處造假“古建”,湖南修炎帝陵、舜帝墓尤其熱心,而有案可稽有字為證,在中國現(xiàn)代化歷史上有紀念碑意義的這一處故址,卻一直不被重視,真不能不使人嘆息。
我總希望有誰能拿出修三皇五帝陵墓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錢,為“時務學堂故址”留一紀念。為當局諸君計,能借梁啟超、譚嗣同、黃遵憲、陳氏父子和蔡鍔諸人的大名,豈不可以大大提高湖南和長沙的知名度,也不必再和廬山去爭朱熹,和成都去爭杜甫了。此事曾與屋主人陳先生談及,他亦首肯。
陳先生名云章,字思默,長我二十歲。數(shù)月前曾往訪,并攝影留念,我自己還在梁啟超題碑前單獨照了一張。
(二零零四年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