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香》劉海鳴散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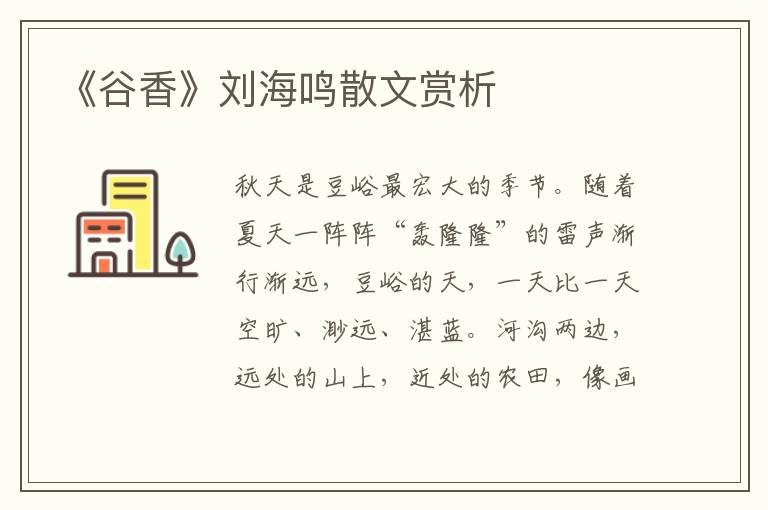
秋天是豆峪最宏大的季節。
隨著夏天一陣陣“轟隆隆”的雷聲漸行漸遠,豆峪的天,一天比一天空曠、渺遠、湛藍。河溝兩邊,遠處的山上,近處的農田,像畫家筆下的油畫,正在由淺入深變成七彩。蟬鳴在正午也沒有夏天那樣聲嘶力竭,尾音顯得疲憊不堪。悶熱潮濕被東南風吹得無影無蹤。早晨起來,仰頭一望,大嶠崖頂上的黃櫨在農人的不知不覺中,已在慢慢地由黃泛紅。
風柔柔地撫摸著沉甸甸的谷穗,帶著糧食的體香隨風飄散,抵達我的味覺。谷穗的清新淡香,令我感念蒼天厚土賜予我們糧食的同時,也使我對土地、勞動這些字眼充滿敬畏。
十七八時,我常常在勞作的間隙坐在半山腰巡視漫山遍野的谷子,像一位久經戰陣的將軍,在檢閱他的士兵。豆峪每條溝的層層梯田里綠波蕩漾,高低起伏,喧嘩騷動。我時常無限夸大對即將成熟的谷子的想象,希望這種植物綿延千里,寬闊無邊。
“麥宜深,谷宜淺,豆子只須蒙住臉”。這是父親教我種植農作物的一句口訣。一場春雨過后,在布谷鳥那啾啾而略帶凄涼的叫聲中,溝里梯田中就傳來漏斗蛋撞擊漏斗的“嗒嗒”聲,農人年復一年播種希望的勞作又開始了。牛牽,驢拽,人拉,谷粒經過耬腿鉆入溫暖、潮濕、暄騰騰的土地;緊接著,農人就會順著谷壟蹴踏剛剛入土的種子。蹴踏是一項技術活兒,眼睛要盯緊腳下,雙腳要用力均勻,且腳印不留空隙。農人蹴踏谷子種子的時候,其身形真是千姿百態。因為要把所有的力氣用在腳底,全身不由自主地有節奏感地上下晃動。有雙手抱在胸前的,有拤腰的,還有雙手背在后面拿著鐮刀的——這是在打土坷垃。
是勞動,似舞蹈。
谷苗剛鉆出土地,密密匝匝,清新而柔軟,一道道嫩綠的線條在田地里搖曳。隔不了多久,農人就開始間苗了。間苗有兩種方式,土話叫,壕谷和埯谷。壕谷一株一株等距離延伸,埯谷則一墩一墩等距離排列。壕谷全憑手工間苗,埯谷則在飛舞的鋤頭下,使一行行密密匝匝的谷苗變成一墩一墩,像抱著團的小孩。谷子在秧苗期,宛如一群天真無邪的懵懂的孩子,等距離一行行或一蔸蔸地迎風站立在豆峪溝溝岸岸的土地之上。
“六月六,看谷秀”。農歷六月份,過膝的谷子頭上就緩緩冒出毛茸茸的谷穗兒來,類似狗尾巴草的模樣(谷子和狗尾巴草均屬禾本科,狗尾草屬)。這時谷子通體的顏色由淺綠變成了深綠,宛如翩翩少年英姿颯爽。它們在青山、草坡、柿子樹、戰備渠以及飛鳥的身體下時隱時現,給我以真情實感。在我的腦海中,“谷子”這個詞成了世界上最美麗的字眼兒。
麥黃大半天,谷黃一袋煙。時序到了立秋,谷稈子一天天茁壯起來,谷穗兒的粗細長短已基本成形,飽滿的谷粒瓷實實的。夏天仰著頭東張西望的谷穗兒羞澀地低下了頭,顯示出它謙遜、內斂的秉性。它們在向太陽感謝,向大地致敬,向農民傳遞豐收的訊息。
軟柿紅了,酸棗紅了,花椒紅了,又一個豐腴的秋天來臨了。
摘花椒的間隙,父親坐在樹下抽煙,面前青煙繚繞,看著一地的谷子,計算著秋后的收成,臉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摘完一棵花椒樹走向另一棵花椒樹,我擓著籃子慌里慌張趟過密集的谷子中間,被身體碰撞的谷子東搖西晃,谷葉子摩擦發出窸窸窣窣的響聲;被腳踩倒的谷子東倒西歪,發出“咯叭、咯叭”類似骨折的響聲。這令人心痛的聲音,使父親猛地站起來,耷拉著臉,厲聲呵斥。
陽光、氣候、時間使谷子通體由墨綠走向深綠,由深綠過渡到淺綠,由淺綠漸漸變成淡黃。這時的谷葉子,黃綠相間,像一個人的中年,成熟,大氣,又不失低調,恬淡,看上去有了別樣的風度氣質。在你不經意間,風把谷稈子抽干了水分,葉子枯干發出沙沙沙沙的摩擦聲,太陽極有耐心地把谷穗鍍成金黃。晚秋的谷子地充盈、富態、平實而又深沉,有一種飽經滄桑的樸素感。
鳥兒嗅到了谷香,它們從樹上草叢成群結隊飛來,分享這豐收的果實。麻雀最多,嘰嘰喳喳,唱著五音不全的歌兒,上躥下跳,令人討厭。某一家人的谷子地里,扎起了谷草人。草人頭上畫著各式各樣的臉譜,它們穿著寬大的、顏色鮮艷的(舊)上衣,帶著(破)草帽,在風中舞蹈,試圖恐嚇飛鳥不要來糟蹋谷子。農人的這些小伎倆,剛開始還起些作用;過不了幾天,麻雀用實際行動在谷草人的頭上胳膊上拉屎尿尿(麻雀撒尿嗎?我還真不知道),嬉戲玩樂,極盡嘲弄。
農人、谷地、麻雀、谷草人,這些鄉村元素,成了我童年記憶中模模糊糊的印象派畫作。
七月底,濁漳河兩岸的雨蒙蒙綿綿。經過雨水和陽光的輪番滋潤,熟透了的谷子在秋陽的照耀下,谷脖子彎成了反U形墜向一邊,谷穗兒握在手中,飽飽滿滿很有質感。要不是它們互相攙扶抱成一團,我真擔心單個一株谷子會頭重腳輕一頭栽倒在地。某種意義上,谷穗、谷粒抑或黃澄澄的小米具備了黃金的品質。
收割開始了。
天剛亮,“欻啦、欻啦”的磨鐮刀聲在村莊響起,絳紫色的磨刀石上,鐮刀在上下摩擦,紫汪汪的水流了一地。刀刃在陽光的反射下,閃著寒光。父親卯足了勁兒,準備兩三天把谷子全部收回來。割谷子這活計真是太累了。腳要站穩,擰轉左臂,掌心向外,抓牢谷把子,順三壟或六壟割下去。彎腰,割斷,扭腰,放把子,這一套簡單而單調的動作要機械地重復一天,即使被村人冠以“好勞力”的父親,一天的谷割下來,也是累得夠嗆,動不動就想和我們發脾氣。說起割谷,老實講,我不是特別擅長。累不少受,還沒別人割得多,這些都還在其次,主要是自己心里覺得沒面子。還有就是腰痛,準確說也不是腰痛,是腰困,割一會兒,就得直直腰,剛覺得舒服些,父母看落下我很遠,數落說,不怕慢,但怕站。我說,腰痛。母親說,小孩兒哪有腰?
弄得我內心十分糾結,甚至沮喪。要說割谷有什么好處,除了收獲糧食之外,還能看豆峪四周花花綠綠的山,想一些美好的事情;能聽鐮刀割斷谷子根部的剎那發出的“嘭嘭”聲,我醉心于這種使我心安理得的響聲,百聽不厭。
谷子割倒,打好捆子,就該扛谷捆子了。豆峪真正的平地沒多少,基本上都是山坡地,小平車到不了的地方,還得人扛。五六十斤的谷捆子忽沙忽沙扛在肩上燥熱難耐,全身的血好像都涌到了臉上,脖子后面摩擦出了血道道。扛谷捆子,別人的確切感受,我無從得知,不過,從“己所不欲”的角度推理,肯定也好受不到哪里去。脖子、臉上剌破的血道道和著咸咸的汗水火辣辣的痛,汗水再流進眼眶,世界顯得迷茫茫一片。有時,我會悲觀地想,農人真是不容易,為了吃口飽飯,弄出這無數勞身費神的事體。旋即,這種想法又被豐收的喜悅所取代。
是啊,對農人而言,這世界上還有什么事情比豐衣足食更讓人內心踏實、精神優雅呢!
我一直很自信地認為,在我們生活的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上,上黨的土壤、氣候最適宜谷子生長,出產的小米具備了優秀的品質。譬如:沁州黃。令人擔憂的是,谷子的種植面積年年縮減,在我們豆峪村,成片成片的谷子地已難得一見。
我曾多次看到毛澤東主席戴著草帽、滿面笑容、站在谷子地里手握谷穗兒的照片。那是偉人與土地的親密接觸,領袖與谷子的熱烈互動。透過照片里的細節,我讀懂了主席對谷子深深的熱愛。
對于谷子這種植物,我有著難以言表的述說。每每看到谷子的圖畫和有關谷子的文字,心中就會升起別樣的情感,我會一次又一次與我的少年時代邂逅,并在其間長時間徜徉,重溫谷子給予我的愛與溫暖。
某一天夜晚,整個小區突然斷電,屋里一片漆黑,躺在床上,無端陷入對谷子的懷想之中。
秋陽高照,天朗氣清,豆峪的溝溝洼洼谷浪涌動。我腳踩松軟的田塍,穿過密集蓬松的谷子地,去欣賞谷子宏大的輝煌和錦繡。東南風吹過,平展展的谷地翻起波浪,蕩起漣漪,耳畔沙沙作響;風過后,它們又恢復從容、篤定、生機勃勃的常態。站在高處遠望,漫山遍野,層層疊疊,像鋪了一地黃綢緞,又像鋪了一地澄黃的金子,在山腰上纏繞,在河溝里舒展,在村莊周圍輾轉、逗留。眨眼間,谷子又翻山越嶺爬上高高的山巔,在村莊的頭頂上鋪陳,把一村人的笑臉都染成了一片淡黃。驀然間,一頂草帽從大嶠崖的高處徐徐飄落,飄落,飄落,它始終沒有落下,一直在豆峪的高空中,在時間的流逝里慢慢下落,連同著谷子的馨香,一直彌漫在我呼吸的空氣里,經久不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