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藝美學要略·論著·《閑情偶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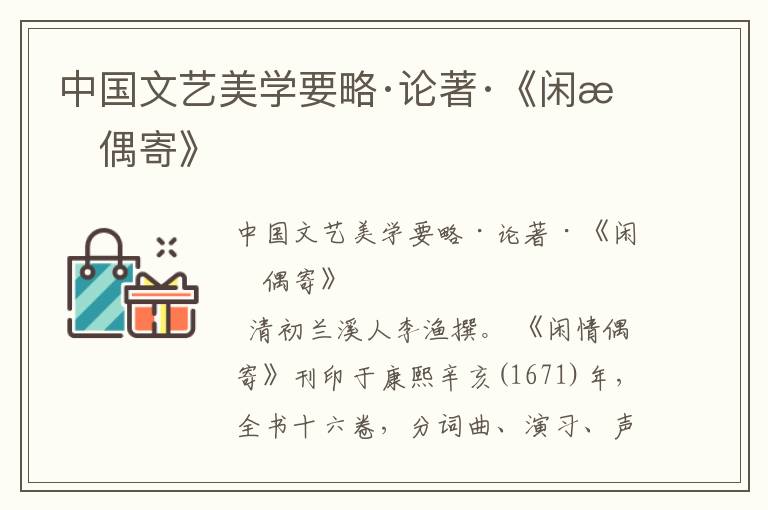
中國文藝美學要略·論著·《閑情偶寄》
清初蘭溪人李漁撰。 《閑情偶寄》刊印于康熙辛亥(1671)年,全書十六卷,分詞曲、演習、聲容、居室、器玩、飲饌、種植、頤養八部。據自序稱,作者意在總結規律,示人以法。但只有“詞曲”、 “演習”兩部所論戲曲美學,最有學術理論意義。現在習見的《李笠翁曲話》是后人將這兩部分單獨刊印成書的。
“填詞之設,專為登場”。李漁論曲十分強調要從觀眾出發,注意戲曲的舞臺演出特點。他認為這是戲曲文學區別于其它文學體裁的一個重要標志;戲曲文學的成敗得失,最終應由觀眾作出評價。所以劇作家劇本不能離開舞臺演出的實際需要,應努力做到“手則握筆,口則登場,全以身代梨園,復以神魂四繞,考其關目,試其聲音,好則直書,否則擱筆”。要求劇本“觀聽咸宜”,這不僅填補了歷來曲論重“曲”不重“戲”的不足,同時也是對明代中葉以來文人傳奇忽視舞臺演出創作傾向的一種療救。李漁突破“填詞首重音律”的習慣看法,把戲曲結構提到“獨先”、 “首重”的位置。他用“造物賦形”和“工師建宅”作比喻,來闡明結構之極端重要,指出戲曲結構之妥善完整與否,直接關系到劇本能否搬上舞臺, “嘗讀時髦所撰,惜其慘淡經營,用心良苦,而不得被管絃、副優孟者,非審音協律之難,而結構規模之未善也。”所以李漁接受他人的經驗教訓,既注意劇曲的布局、章法等局部的結構問題:又進而把注意力集中到“結構全局規模”,開始研究戲曲的藝術構思和矛盾沖突;在“結構第一”章下,深入討論“立主腦”、“脫窠臼”、 “密針線”、 “減頭緒”、 “戒荒唐”諸問題,第一次明確提出研究戲曲結構美的課題。
“立主腦”是李漁結構論的主干。“主腦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劇中為主的“一人一事”,如《琵琶記》中蔡伯喈“重婚牛府”,《西廂記》中張君瑞“白馬解圍”這樣的主要人物和重要情節,就是它們的“主腦”。他以為沒有主腦的劇本不過是斷線之珠,無梁之屋,缺乏藝術的完整美。 “立主腦”離不開“減頭緒”和“密針線”。一個頭緒紛繁旁見側出之情甚多的劇本,其戲劇沖突必然枝蔓不清, “主腦”不立。待到頭緒既簡,還需“針線”緊密, “編寫有如縫衣,其初則以完全者剪碎,其后又以剪碎者湊成。……湊成之工,全在針線緊密,一節偶疏,全篇之破綻出矣。”這些見解都精辟地揭示了戲曲結構的藝術奧秘。
關于戲曲創作的“虛”、“實”問題,李漁用“姓名事實,必須有本”,和“傳奇無實,大半寓言”相結合的辦法加以調整。 可是,“有本”并非照搬照抄,更不是拾人牙慧; “無實”也不是憑空杜撰,荒誕不經。而是有所選擇、剪裁,達到“既出尋常視聽之外,又在人情物理之中。”
李漁很重視“新”、 “奇”和“變”。 “新也者,天下事物之美稱也”;“新,即奇之別名”;“非奇不傳”,唯有創新出奇,戲曲才有持久的藝術魅力。他看到戲曲與詩文一樣,隨著時代的演進而不斷變革,決不停滯不前,凝固不變。“變則新,不變則腐;變則活,不變則板”,深刻地剖析了“新”與“變”的內在聯系,說明創新寄寓于變更之中。
李漁論述戲曲語言,重視賓白,批評那種“視賓白為末著”的偏見。認為設計人物語言, “但宜從腳色起見”,和劇中的腳色行當相合拍;把人物的內心活動和個性特征表現出來, “說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弗使浮泛”。劇中語言力求雅俗共賞,既通俗易懂,又有藝術感染力,便于演員“上口”念唱,便于觀眾“入耳”鑒賞。
“演習部”所論大都涉及戲曲導演方面的問題,為劇目選擇、劇情處理、演員遴選、腳色分派、念唱表演以及舞臺調度、音樂、舞美的組織運用等,都是前人甚少論及的。
最后, 《閑情偶寄》關于戲曲理論組織體制的貢獻也值得一提。“詞曲”、 “演習”兩部之下設若干章,各章都有總論性的序言,章之下又有若干小節,各節標以醒目的論題。這“部”、“章”、“節”的區分,反映了作者在理論的明確性和系統性上,比他的前人有了一個飛躍。 在兩“部”,十一“章”, 五十三小“節”里,囊括了戲曲理論的主要問題。它不再是隨筆雜感式的舊體制舊模式,而是把它組織得有綱有目,層次井然,輕重分明,從而開拓了我國古典戲曲理論組織體制的新生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