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論的運用《形象化議論》文學寫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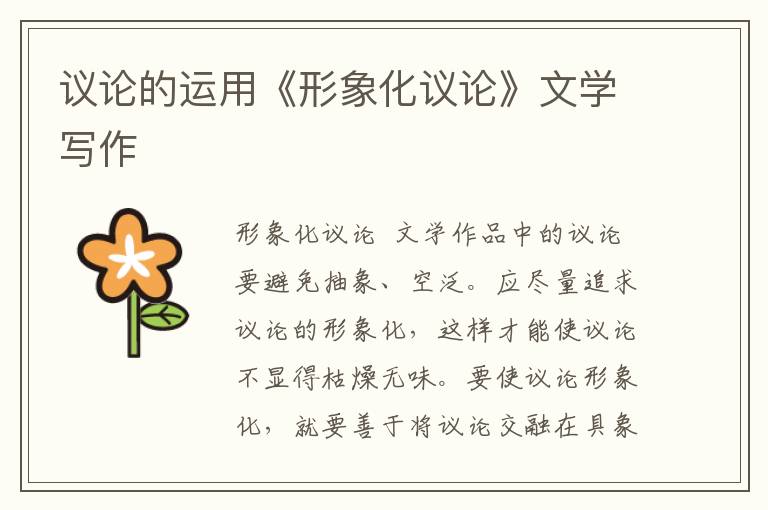
形象化議論
文學作品中的議論要避免抽象、空泛。應盡量追求議論的形象化,這樣才能使議論不顯得枯燥無味。要使議論形象化,就要善于將議論交融在具象而生動的描寫中,以象中有議、議中有象的方式進行。如徐剛的散文《扶花惜草也是愛》:
夏天的夜晚是芬芳而迷人的。
一天的工作總使人感到心神疲倦。因此,我愛在下班以后到公園走一走。月光下,是那么多的小草,多么多的花朵,那么多的青枝綠葉;林蔭小道又是如此安靜,就連身邊一對對戀人的纏綿細語也像抒情詩一般優美。
夜幕中的公園真像是奇妙的花房,愛情的花朵往往是在此時此地開放的。是的,勞動者的驕傲不僅僅是在于白天的辛勤與創造,也在于:熱愛夜晚的恬靜,珍惜自然的美,敢于大膽地愛——這是活生生的世界的一個活生生的組成部分。不準愛,不許愛,連愛情也遭放逐的日子過去了!——那是嚴寒的冬日,人人都要穿著厚厚的棉衣,把靈魂包裹著,把心的門窗關閉著。
如今,夏夜的公園里有很多、很多的愛。戀人們偎依著,傾訴衷腸,這當然是愛;母親抱著牙牙學語的孩子數天上的星星,這也是愛;那三五成群在樹蔭下談笑的退休工人,不也充滿了對生活的愛嗎?
不知是誰折斷了幾朵剛剛含苞的紫云英,還有幾朵白的月季和粉紅的芙蓉花也散落在路旁。有一個在路燈下能看出。已經須發斑白的園林工人把它們撿起,然后,走到花圃前,細細地察看著,像梳理自己小孫女兒的頭發那樣,整理者被攀折過的花木的枝葉。在公園里,我不止一次地目睹過這種情景,看見了一種對生活的執著的愛,一種甚至更為廣大的愛。
這是園丁的愛!
往戀人的辮梢上插一朵花,或者是包在她的手絹里,這是很有點詩情畫意的。但,辮梢和手絹畢竟不是土地,小花兒很快枯萎了,于是又像冰棍紙一樣,被順手棄之路旁。而園林工人的心卻被損害了!還有許多的戀人,看著這夭折的落英,心情大概也不會好的。
其實,小花小草雖小,卻也自有其崇高的一面——它們的活著并不是為了自己的延年益壽,而是為了讓生活有更多的光彩和芬芳——是為了別人而活著的,是屬于整個世界的。
難怪園林工人要生氣了。“芟夷枝葉的人決然得不到花果”,有了更多的愛,才能收獲更多的花。
扶花惜草也是愛!
(選自楊廷治《一分鐘散文小說選讀》,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1年版)
這篇散文穿插了一些議論,讀者讀到這些議論文字時并不感到乏味,反而增添了閱讀的興趣和加深了對作品立意的理解。“不準愛,不許愛,連愛情也遭放逐的日子過去了!——那是嚴寒的冬日,人人都要穿著厚厚的棉衣,把靈魂包裹著,把心的門窗關閉著。”這樣的議論不是抽象枯燥的,而是借用了“嚴寒的冬日”、“厚厚的棉衣”、包裹的“靈魂”、“關閉著心靈的窗戶”等富有象征意味的形象,使議論變得靈動有力,耐人尋味。“往戀人的辮梢上插一朵花,或者是包在她的手絹里,這是很有點詩情畫意的。但辮梢和手絹畢竟不是土地,小花兒很快枯萎了,于是又像冰棍紙一樣,被順手棄之路旁。而園林工人的心卻被損害了!還有許多的戀人,看著這夭折的落英,心情大概也不會好的。”這樣的議論也不會讓人感到乏味,它借助于往戀人辮上插花、手絹里包花的生活現象,又借助于很快會枯萎的花兒將像冰棍紙被扔到路旁的比喻,使議論形象化,使批評、告誡委婉含蓄,讓讀者樂于接受這樣的說理。
由此可見,使用比喻是使議論形象化的重要手段。上文被采摘的花兒很快枯萎,容易被當作冰棍紙一樣的垃圾而被扔掉,就是形象地提醒人們不要掠奪花的美麗,再美麗的花朵離開了母體將很快黯然失色、失去價值。因為使用比喻這種修辭常常能使陌生的變得熟悉、高深的變得淺顯、抽象的變得形象,所以,作家常常在文學作品中借用比喻修辭來發議論、作評價、表達見解和主張。例如,朱自清《匆匆》,“在逃去如飛的日子里,在千門萬戶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罷了,只有匆匆罷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過去的日子如輕煙,被微風吹散了,如薄霧,被初陽蒸融了;我留著些什么痕跡呢?我何曾留著像游絲樣的痕跡呢?我赤裸裸來到這世界,轉眼間也將赤裸裸的回去罷?但不能平的,為什么偏要白白走這一遭啊?”對于時間是怎樣“匆匆”流逝,詩人并沒有作抽象的議論,而是把自己的感覺和潛在的意識通過形象化的比喻——“過去的日子如輕煙,被微風吹散了”,“如薄霧,被初陽蒸融了”,“我何曾留著像游絲樣的痕跡呢?”表現出來,“把觸角穿透熟悉的表面,向未經人到的那里”,尋那“新鮮的東西”。
要使議論更加形象,也可以采用擬人手法。尤其是將擬人與比喻結合,議論就更加生動形象。例如,《世說新語·文學》:“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行大法。應聲便為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豉以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慚色。”曹植以“豆”與“萁”“同根生”形象地比喻了曹丕與他同父而生,“萁在釜下燃”比喻曹丕煎熬、逼迫他走投無路、陷入絕境,而且“豆在釜中泣”的“泣”則以擬人手法形象地揭示了詩人內心的痛苦和對親情的失望。
要使議論更加形象,還可以采用類比論證。與比喻中本體和喻體關系不同,類比中主體和客體兩個事物在整體上可以是同類的。在成語故事“葉公好龍”(漢·劉向《新序·雜事五》)中,子張將形式上“好龍”實際上“怕龍”的葉公與宣稱“好士”但實際上根本就不把真正的“士”放在眼里的魯哀公進行類比,諷刺了魯哀公只唱高調、不務實際。“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也提到了這個典故:“嘴里天天說‘喚起民眾’,民眾起來了又害怕得要死,這和葉公好龍有什么兩樣!”
形象化的議論,還可以巧妙利用日常生活場景的變化與對比來實現。例如,陳忠實《白鹿原》:“饑餓比世界上任何災難都更難忍受,鴉片煙癮發作似乎比饑餓還要難熬,孝文跌入雙重渴望雙重痛苦的深淵。博大紛繁的世界已經變得十分簡單,簡單到不過一碗稀粥一個蒸饃或者一只烏紫油亮的煙泡兒。當小娥掃了瓦甕又掃了瓷盆,把塞在窯洞壁壁洞里包裹過鴉片的乳黃油紙刮了再刮,既掃不出一星面也捏捻不出一顆煙泡的時候,那個冬暖夏涼的窯洞,那個使他無數次享受過人生終極歡愉的火炕,也就頓時失去了魅力。”通過日常生活的呈現,將曾經的歡愉與現在的困頓、窘迫、乏味對比,并把饑餓、煙癮的難熬與災難作比較,自然而然地寄寓了作者的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