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的文學主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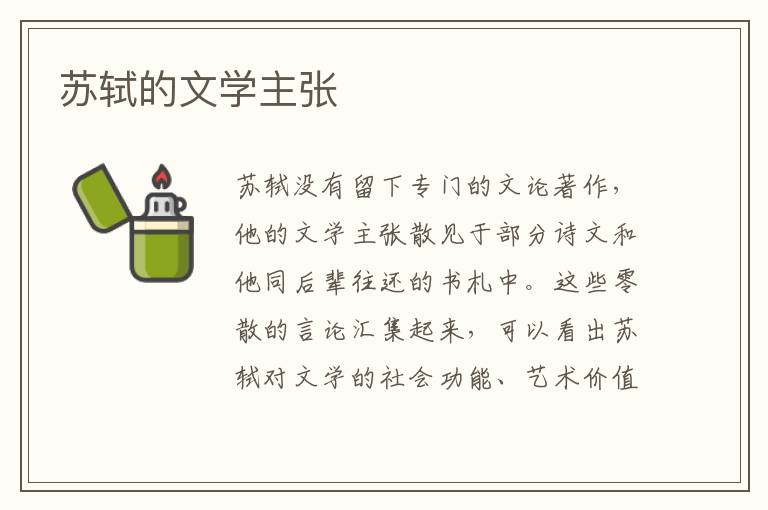
蘇軾沒有留下專門的文論著作,他的文學主張散見于部分詩文和他同后輩往還的書札中。這些零散的言論匯集起來,可以看出蘇軾對文學的社會功能、藝術(shù)價值、創(chuàng)作規(guī)律等重大問題都有獨到的認識和精辟的見地。
蘇軾重視文學的政治作用和社會功能。他強調(diào)文章要“有為而作”,遵循其父蘇洵“言必中當世之過”的教導,講求詩文的實際效果,排斥抵制形式主義的文風。他在散文方面以韓愈為師,說韓愈“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在詩歌方面則對杜甫推崇備至,說“古今詩人眾矣,而杜子美為首”;在詞方面,他主張打破詩與詞的界限,反對詩莊詞媚的傳統(tǒng)說法,認為詞中“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開拓了一條“以詩為詞”賦予詞以嚴肅主題的新路。
蘇軾對文學的藝術(shù)價值有正確的認識和闡述。他繼承了歐陽修的觀點,對文與道的關(guān)系作了切合實際的說明,認為二者是結(jié)合而非從屬的關(guān)系。對道的理解,蘇軾也更寬泛,除了治國之道,他更重視文章之道,即文學的藝術(shù)價值。他反復強調(diào)“辭達”,發(fā)揚了儒家傳統(tǒng)的文學觀點,說“辭至于達,足矣,不可以有加矣”。這就不再是象韓愈那樣僅僅把文看作載道的工具了。蘇軾引用歐陽修把文章比喻為“精金美玉”的言論,也可看出他對文學自身藝術(shù)價值和美學價值的重視。
蘇軾對文學創(chuàng)作的某些規(guī)律也作了探索。他主張作家為文先要“了然于心”,有了創(chuàng)作沖動才能寫出好的詩文。他強調(diào)立“意”,重視內(nèi)容,也認為要有與內(nèi)容相適應的不同的形式。進入寫作時,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無定質(zhì),但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也就是在“求物之妙”把握描寫對象的本質(zhì)之后,自由揮灑,不拘一格,擺脫各種清規(guī)戒律的束縛。基于此,蘇軾認為詩、詞、文應該有多樣化的藝術(shù)風格,不能人為劃一,正如世間的美女肥瘠各異卻各具姿質(zhì)一樣,文學的風格也該各呈異彩,各具其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