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藝美學要略·學說與流派·不涉理路,不落言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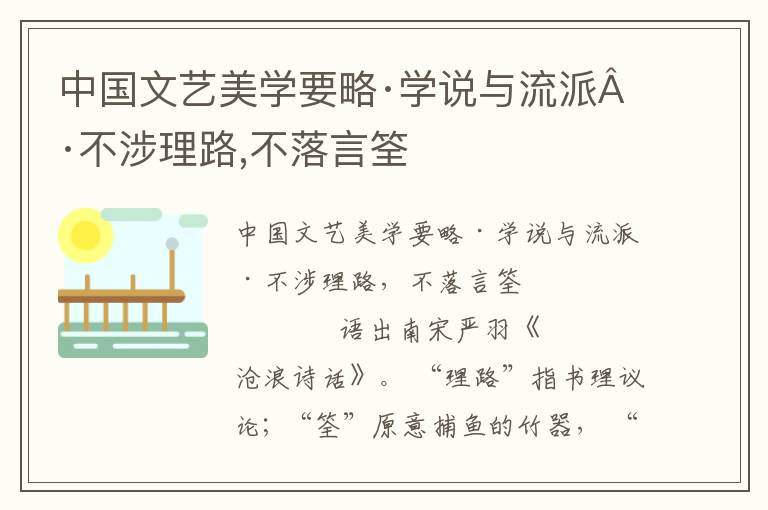
中國文藝美學要略·學說與流派·不涉理路,不落言筌
語出南宋嚴羽《滄浪詩話》。 “理路”指書理議論; “筌”原意捕魚的竹器, “言筌”是指文字考據一類的因素,莊子有“得魚忘筌”之說。這里整句是說詩歌創作是一種特殊的思維活動,即似于我們現在的形象思維,是與邏輯思維截然不同的“別材別趣”。
嚴羽提出“不涉理路”,有反對宋時理學家以理語為詩和江西詩派以議論為詩的意圖,后者在詩歌創作中體現了過分明顯的理論思維,從而破壞了詩的意境。而“不落言筌”。則是有意反江西派“用字必有來歷、押韻必有出處”的掉書袋習氣,后者把寫詩看作是一種文字和書本工夫,破壞了詩歌意象的創新。嚴羽要求擺脫“理路”、“言筌,”所創造的是 “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詩境,提出了藝術表現不應太實太切、而應該不即不離、不粘不脫的主張,并以為詩歌欣賞主要是一種不能分析的直覺經驗。
但“不涉理路,不落言筌”并不是反對讀書,讀書不但不妨礙作詩,有時反有幫助;理也不妨礙詩境之妙,有時會有助于對事物的深入觀察,所以嚴羽又說古人并不排斥讀書窮理。問題在于書如何讀,理如何用。為此,嚴羽提出了學習作詩的基本方法,一是從前代到后代的閱讀順序,二是平時讀書的“秒悟”。“妙悟”才能使自己不受“理”和“言”的約束;一個“悟”字,終于又將詩歌的特點與書理考據區別開來。變前人的東西為自己主觀的感受,獲得了創新的契機。
“不涉理路,不落言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詩歌創作與欣賞的形象性、直覺性特點,它主要是從禪教中受到啟發,但也基于前人對文藝的一些看法。莊子有“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無言而心說”之說,皎然有“但是性情,不睹文字”,司空圖有“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梅堯臣有“言有盡而意無窮”,都可看作是嚴羽之說的淵源。而往后,則有神韻說、性靈說又都受到嚴羽之說的影響。并形成中國詩學上源遠流長的一派,與主現實、重理性的一派形成對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