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入行·李白》原文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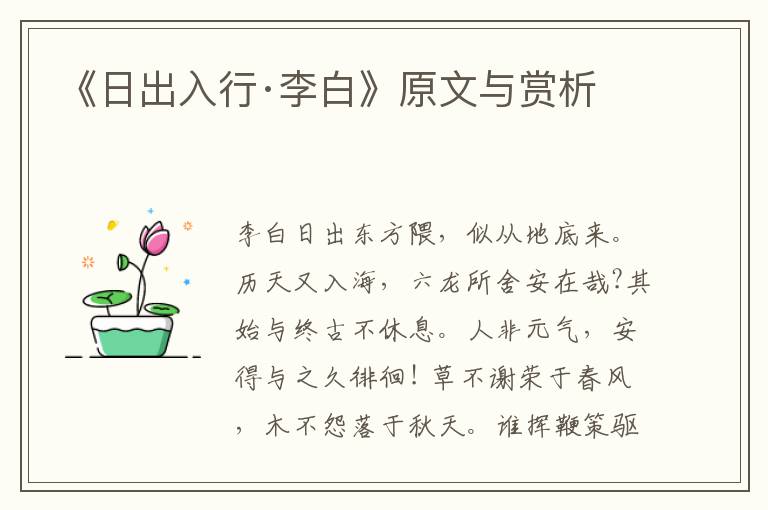
李白
日出東方隈,似從地底來(lái)。歷天又入海,六龍所舍安在哉?其始與終古不休息。人非元?dú)猓驳门c之久徘徊! 草不謝榮于春風(fēng),木不怨落于秋天。誰(shuí)揮鞭策驅(qū)四運(yùn),萬(wàn)物興歇皆自然。羲和,羲和! 汝奚汨沒(méi)于荒淫之波?魯陽(yáng)何德,駐景揮戈?逆道違天,矯誣實(shí)多。吾將囊括大塊,浩然與溟涬同科。
李白這首詩(shī)認(rèn)為日出日落、四時(shí)更替,都是客觀自然規(guī)律的表現(xiàn),人不能超越和違背自然規(guī)律,只是遵循規(guī)律,聽(tīng)任自然。這種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熠然生輝,因而它在《李太白集》中為別具一格之作。
詩(shī)的前六句寫(xiě)日出日落,是它自身的運(yùn)行規(guī)律。日出東方,墜于西方,本為地球本身自轉(zhuǎn)所致,作為恒星的太陽(yáng)并不作從東到西的運(yùn)動(dòng)。可是在人們尚未認(rèn)識(shí)天體的究竟時(shí),極易誤以為日出扶桑,沒(méi)于西海。古人不能科學(xué)地解釋日、地運(yùn)行規(guī)律時(shí),更以為是日神羲和駕著六條龍拉的車(chē)載著太陽(yáng)在行走。李白說(shuō)日出“似從地底來(lái)”,以疑似的口吻敘說(shuō),雖沒(méi)有能說(shuō)破太陽(yáng)與地球的關(guān)系,但已對(duì)地作為一個(gè)“大塊”產(chǎn)生了懷疑。而“六龍所舍安在哉”,則明確地對(duì)六龍的存在表示了否定。日出日落,說(shuō)是羲和車(chē)載運(yùn)送,那他的六條龍又住在什么地方呢?日的運(yùn)行,終古不息,人并非“元?dú)狻保趺纯梢耘c它長(zhǎng)久地在一起。元?dú)猓覈?guó)古代哲學(xué)家常用術(shù)語(yǔ),認(rèn)為它是最原始、最本質(zhì)的因素,渾沌一片,浩瀚無(wú)邊,天地萬(wàn)物都是由它派生出來(lái)的。人不是這種元?dú)猓窃趺纯梢院吞?yáng)永遠(yuǎn)共存同游呢!李白在否定太陽(yáng)由外力駕馭的同時(shí),同時(shí)也正視了天地的長(zhǎng)久,人的短暫。人只是在日出落的長(zhǎng)期過(guò)程中,一段時(shí)間的停留于世。神不會(huì)駕日,人不可久世,這是自然規(guī)律。
中間四句講“萬(wàn)物興歇皆自然”。草木春天繁榮,秋后衰敗,好象春風(fēng)、秋天使之如此。詩(shī)人說(shuō)“草不謝榮于春風(fēng),木不怨落于秋天”,不謝、不怨,也就是說(shuō)草木自有其本身的生長(zhǎng)規(guī)律,不是客觀有什么力量主宰著。當(dāng)然,草木榮衰和春秋的季節(jié)有關(guān),可是這季節(jié)的更迭又不是有神力在支配,它也無(wú)意于榮衰草木,所以也就談不上要“謝”與“怨”了。為了說(shuō)清這個(gè)意圖,詩(shī)人點(diǎn)明了物理:“誰(shuí)揮鞭策驅(qū)四運(yùn),萬(wàn)物興歇皆自然。”是誰(shuí)在那里驅(qū)使著四季運(yùn)轉(zhuǎn)?自然不是羲和等神明,一切生物的盛衰榮枯,都是它們自然之理。詩(shī)人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于此光華四射,炫人眼目。詩(shī)人以問(wèn)領(lǐng)起,激人遐想,以截然之語(yǔ)作答,理足語(yǔ)沉,毋庸置疑。
最后八句,在否定馭日的傳說(shuō)時(shí),導(dǎo)出順應(yīng)自然的本旨。要說(shuō)羲和駕六龍以載日,那么怎么會(huì)沉沒(méi)到浩淼無(wú)際的波濤中去呢?要說(shuō)魯陽(yáng)公,又怎么會(huì)揮戈止住太陽(yáng)下山? 《淮南子·覽冥訓(xùn)》說(shuō)魯陽(yáng)公與韓作戰(zhàn),十分激烈,時(shí)近黃昏,魯陽(yáng)公持戈一揮,使太陽(yáng)退后三舍(一舍合三十里)。羲和駕日固不足信,魯陽(yáng)止日,也屬荒誕,這些都是“逆道違天”的矯誣之說(shuō)。詩(shī)至此,將自然運(yùn)行規(guī)律不依傍客觀力量的道理說(shuō)足、說(shuō)透。李白認(rèn)為認(rèn)識(shí)并順應(yīng)了這客觀規(guī)律,那就能“囊括大塊”,精神上包羅萬(wàn)有,浩然之氣與“溟涬同科”。溟涬,即元?dú)?同科,同類(lèi)。詩(shī)前說(shuō)“人非元?dú)猓驳门c之久徘徊”,這兒講能和元?dú)庀嗤?lèi)。詩(shī)人的意思是人不能馭自然,也不可役于自然,而是和萬(wàn)物一樣,有其內(nèi)在的自然的發(fā)展規(guī)律,“萬(wàn)物興歇皆自然”。
李白這首詩(shī)本無(wú)意于寫(xiě)自然科學(xué)道理,可是卻很好地道出了科學(xué)原理;也無(wú)意于寫(xiě)人生哲理,可是卻很深刻地揭示了人生哲學(xué)。詩(shī)人原意是表明自己的一種追求,“似為求仙者發(fā)”(《唐宋詩(shī)醇》),可是從日月運(yùn)行、四季更迭、草木榮枯等自然現(xiàn)象的理解上,卻超越了自我,擺脫了苦悶,從應(yīng)順自然中得到啟迪和慰藉,使詩(shī)既以情感人,又以理服人,且以事取信于人,達(dá)到了情理交融、敘議互發(fā)的藝術(shù)境界。漢樂(lè)府《郊祀歌》有《日出入》篇,寫(xiě)的是日出入無(wú)窮無(wú)盡,感嘆人生短暫,幻想騎上六龍成仙上天。而李白則否定六龍駕日,并無(wú)羽化登仙之想,提出“萬(wàn)物興歇皆自然”的命題,這在李白集中屬難得之作,在古代詩(shī)史上也居于令人注目的地位,確是十分可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