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得的夢》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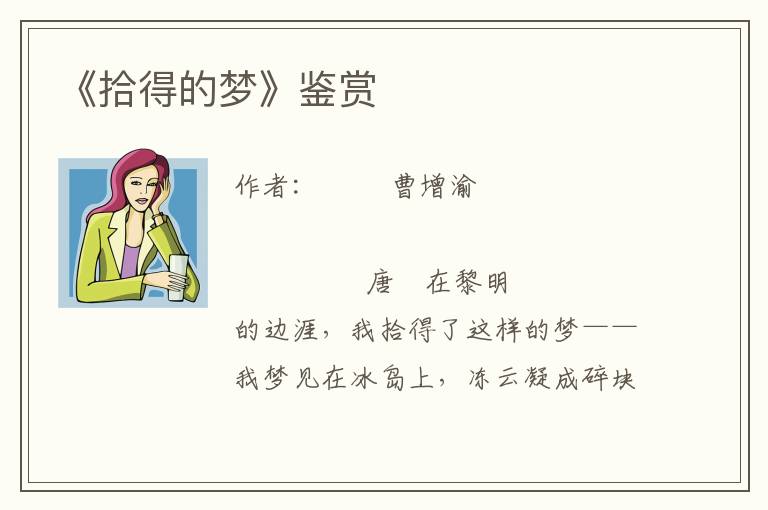
作者: 曹增渝
唐弢
在黎明的邊涯,我拾得了這樣的夢——
我夢見在冰島上,凍云凝成碎塊,依依於陰暗的冰谷。曾經(jīng)為升平而點綴的花草,藤樹,現(xiàn)在卻僵臥在小徑上,萎悴狼藉,凝成了行人的絆腳石。但這里又似乎并無行人,有的只是空漠,是陰森和死寂,連空氣也結成冰柱,我用自己的呵氣溶化它,呼吸這溶化了的一點,聊延殘喘。
有殘喘,也就有呵氣,我活下去。
四圍,紅的波濤中,流蕩著大大小小的冰塊。圓的,象骷髏;長的,象骨骼;隨波起伏。它們在跳舞,在獰笑,擁積在冰島的沿岸,象春天的水面的浮渣一樣,被風帶到了幽僻的一角。
我嗅到了腐臭的氣息,是死狗皮。
我見到了臃腫的形體,是爛豬肉。
那跳動的是主和的舌,那灰白的是卑鄙的心,夾著骷髏,骨骼,隨波起伏。
它們在跳舞,在獰笑。
我始而靜思,繼而沉吟,終于大笑,宇宙也跟著我笑起來,冰柱在這笑聲里溶解,因為,群的笑聲里的呵氣,是和煦的春風,帶著更多的熱意。
一株小草從冰的裂縫里跳出來,無數(shù)株小草從冰的裂縫里跳出來,頃刻,綠遍了全島。
我問:
——春天到來了嗎?
——用我們的力量,帶著它來!
我始而靜思,繼而沉吟,終于大笑,海洋也跟著我笑起來,冰塊在這笑聲里溶解,因為,群的笑聲里的呵氣,是和煦的春風,帶著更多的熱意。
一個浪頭從海的幽邃處卷起來,無數(shù)個浪頭從海的幽邃處卷起來,頃刻,澄清了海面。
我問:
一朝暾上來了嗎?
——用我們的力量,帶著它來!
凍云飛散了,冰谷里冒出奔騰的迷霧。風,溫暖地吹著,澄波映著青天,那上面掛著一個白熱的朝陽,金光染紅了整個宇宙。
冰島在溶解,動蕩,崩裂,……我的腳又踏到了實地。
1939年1月8日
日寇侵華戰(zhàn)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本世紀以來最深重的民族災難。特別是淪陷區(qū)的人民,不但生命財產(chǎn)受到肆意踐踏和嚴重威脅,而且每日每時都在忍受著亡國奴的屈辱。唐弢當時滯留于上海“孤島”,心情的憤激苦悶,可想而知。他的散文詩大多寫于這個時期,自然帶有這個時代和這種特殊環(huán)境的明顯烙印。
有一句外國諺語說:“清晨的夢境能成為現(xiàn)實。”這篇《拾得的夢》止是在對清晨夢境的描繪中寄托著擺脫民族苦難爭取民族解放的熱切期望。
作者在這里描述的夢境與朱大柟的《血的嘴唇的歌》很有幾分相似之處。它們都是以世界的冰凍和融化曲折地表達自己對周圍環(huán)境的感受和內(nèi)心的熱望。然而二者又有明顯的不同。《血的嘴唇的歌》沒有具體的現(xiàn)實針對性,更多地訴說感覺和幻想,是一種飄渺虛幻而又有幾分怪異的境界。這篇《拾得的夢》卻毫不含糊地把批判的鋒芒指向日寇對上海的侵占,指向當時社會上沉滓泛起、群魔亂舞的丑惡景象。它所呼喚的,則是人民力量的奮起,是民族解放斗爭的偉大勝利。
作品中的“冰島”,顯然是指日軍占領下的上海。這是一個陰森死寂、猙獰可怖的世界。路上沒有行人,連空氣也結成冰柱,人們只能靠自己的呵氣溶化一點空氣,“聊延殘喘”。四周那“紅的波濤”當是中國人民灑下的鮮血,那些大大小小的“在跳舞”“在獰笑”的冰塊,正是上海灘上甘心為虎作倀的民族敗類。作者以極其憎惡的心情寫道:“我嗅到了腐臭的氣息,是死狗皮。/我見到了臃腫的形體,是爛豬肉。”“主和的舌”,“卑鄙的心”,“夾著骷髏,骨骼,隨波起伏”。
然而作者并未沉溺于悲憤和絕望。相反,他在“我”和“群”的笑聲中覺察到了“和煦的春風”與“熱意”,覺察到了足以撼動、消解這個世界的力量。于是,他的夢境變了,變得生機勃勃,變得熱氣騰騰,“一株小草從冰的裂縫里跳出來,無數(shù)株小草從冰的裂縫里跳出來,頃刻,綠遍了全島。”“一個浪頭從海的幽邃處卷起來,無數(shù)個浪頭從海的幽邃處卷起來,頃刻,澄清了海面。”這里,他顯然在假托夢境,熱情地呼喚民眾的奮起,呼喚大家“用我們的力量”,去迎接冰化雪消的春天,迎接染紅宇宙的“白熱的朝陽”。
這篇散文詩,藝術上相當完整精粹。充沛的激情和鮮明的意象融成一個有機的整體,不僅具有強烈的戰(zhàn)斗性,而且富于藝術的感染力。縱然在時過境遷的今天,我們也仍然能夠從作品所張揚的那種樂觀堅定的斗爭信念和不屈不撓的斗爭意志中受到生動的啟示,吸取到一種業(yè)已構成歷史傳統(tǒng)的巨大精神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