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書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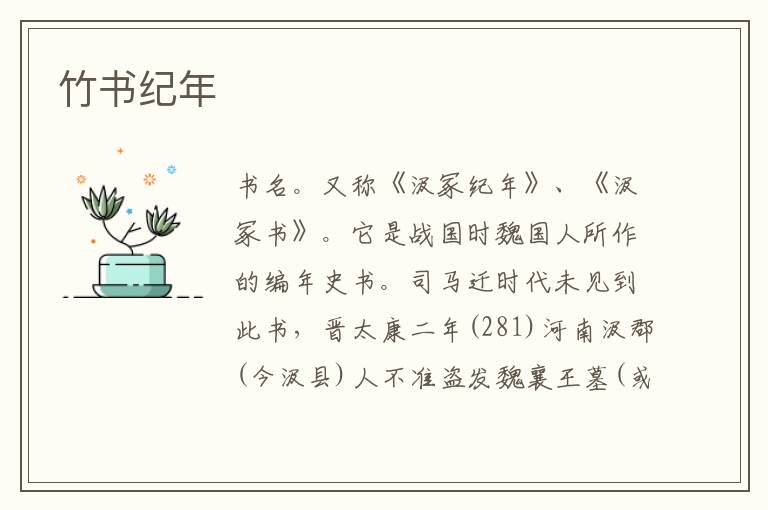
書名。又稱《汲冢紀年》、《汲冢書》。它是戰國時魏國人所作的編年史書。司馬遷時代未見到此書,晉太康二年(281)河南汲郡(今汲縣)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墓),發現了數十車長二尺四寸的竹簡書,大部分都在盜墓時用來照明燒掉了。余下部分有《紀年》十三篇,經束皙、荀勖等當時的學者鑒定,知道是古史書,所記內容自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周宣王以后,只記晉國事,晉三分以后,又特記魏國事,至魏襄王二十年稱“今上”,可見這書是魏襄王時人所作。書中以夏正紀年,以建寅元月為歲首,其文字用古籀,體裁為編年,記事簡短如《春秋》。這書發現以后,為歷代學者所重視,郭璞的《穆天子傳注》,干寶的《搜神記》,酈道元的《水經注》,司馬貞的《史記索隱》,歐陽洵的《藝文類聚》,李善的《文選注》,劉知幾的《史通》,李昉的《太平御覽》,王存的《元豐九域志》,羅泌的《路史》,胡應麟的《三墳補逸》,鮑彪的《戰國策注》,顧炎武的《日知錄》都引證它。但是唐朝以后,人們就看不到它了,這就是古本《竹書紀年》。到了明代,又出現一本《竹書紀年》,據學者考證可能是天一閣主人范欽根據各種古書引征古本《竹書紀年》輯錄的,但有些刪削,也有偽造。古本、今本有何區別?(一)古本敘事起自夏代,今本敘事起自黃帝。(二)古本用夏歷,今本用周歷。(三)古本說“夏年多殷”,今本殷年反多于夏。(四)古本有“益干啟位,啟殺之”,“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今本俱無此說。(五)《梁書·沈約傳》、《隋書·經籍志》都不曾提到沈約注《竹書紀年》,今本所標沈約注語,多采用沈約《宋書·符瑞志》的話,這足證今本是偽托的。《竹書紀年》既為戰國時人所作,因此所記戰國時事就比較正確,其中有些材料與《左傳》所記相一致,司馬遷寫《史記》未見到此書,它可以糾正《史記》的一些錯處。《竹書紀年》中舜囚堯,夏年多殷,啟殺益,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與《經傳》、《史記》說不同,這些不同恰好說明《竹書紀年》的史料價值。清代學者對《古本竹書紀年》作了輯佚工作,成績很大,著名的有王國維的《古本竹書紀年輯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