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藝美學(xué)要略·學(xué)說與流派·陽湖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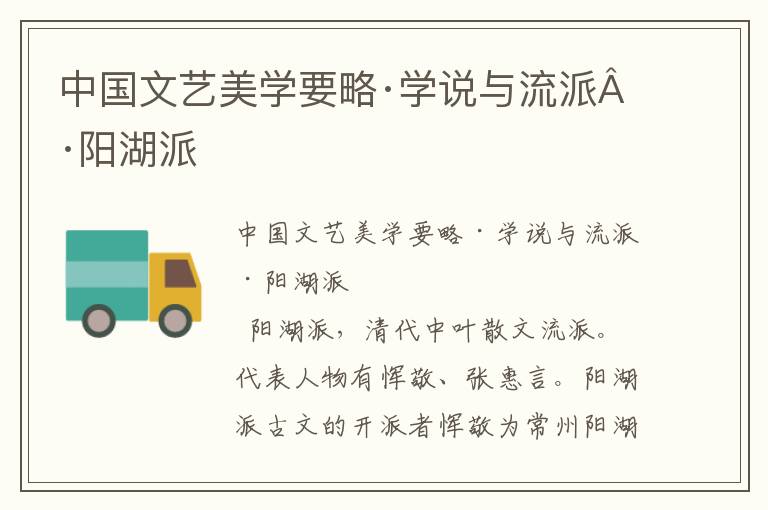
中國文藝美學(xué)要略·學(xué)說與流派·陽湖派
陽湖派,清代中葉散文流派。代表人物有惲敬、張惠言。陽湖派古文的開派者惲敬為常州陽湖人,故名之。
惲敬、張惠言原為桐城派中堅人物劉大櫆的再傳弟子,他們的古文理論與桐城派基本相同。桐城派標舉古文義法,把古文和一般散文區(qū)別開來。方苞說:“辨古文氣體,必至嚴乃不雜也。”惲敬說: “古文,文中之一體耳,而其體至正,不可余,余則支;不可盡,盡則敝;不可為客,為客則體下。”這都是在強調(diào)古文的特殊性,欲令其高出于一般散文之上。由此可見陽湖派與桐城派的繼承關(guān)系,但陽湖派在理論上并非對桐城派亦步亦趨。他們對桐城派一味講求為文的清規(guī)戒律表示不滿,指責(zé)他們不注重內(nèi)在修養(yǎng)與才學(xué)的積累所帶來的文章才力不逮。他們主張增強見識,積累才學(xué),在文章之外下功夫。即所謂“渾然于所為文之外”。而見識、才學(xué)之具體要求是: “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文必足以發(fā)難顯之情。”(惲敬《上曹儷笙侍郎書》中引曾鞏語)惲敬還提出了“天成”與“法度”的關(guān)系。他說: “然此事如禪宗,箍捅脫落,布袋打失之后,信口接機,頭頭是道,無一滴水外散,乃為天成。若未到此境界,一松口便屬亂統(tǒng)矣。是以敬觀古今之文,越天成越有法度。”這就是說如果才學(xué)積累得深厚,見識超人,則信口而言即為至文,有如“天成”。但如果才學(xué)淺薄,見識平庸,則應(yīng)遵法度,不可稍有任意,否則便會出格。由是觀之,陽湖派雖承襲桐城派,但并未囿于桐城派,他們在一些方面突破了桐城派的清規(guī)戒律。在作文方法上他們亦較桐城派通達,主張廣學(xué)古人,不限于一家,并要取長補短,因而于六經(jīng)、史、漢、諸子雜書,各為采擷。在內(nèi)容上,陽湖派主張文章的作用在于闡明“吾人之道”。在這一點上他們自認為是繼承了韓愈的主張的。基于上述這種主張,陽湖派的文章比桐城派開闊,有氣勢,不象桐城派那樣拘泥成法,風(fēng)格枯淡。所以說,在古文理論和古文創(chuàng)作上,從桐城派到陽湖派是一個發(fā)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