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文藝美學要略·流派·歐洲中世紀的美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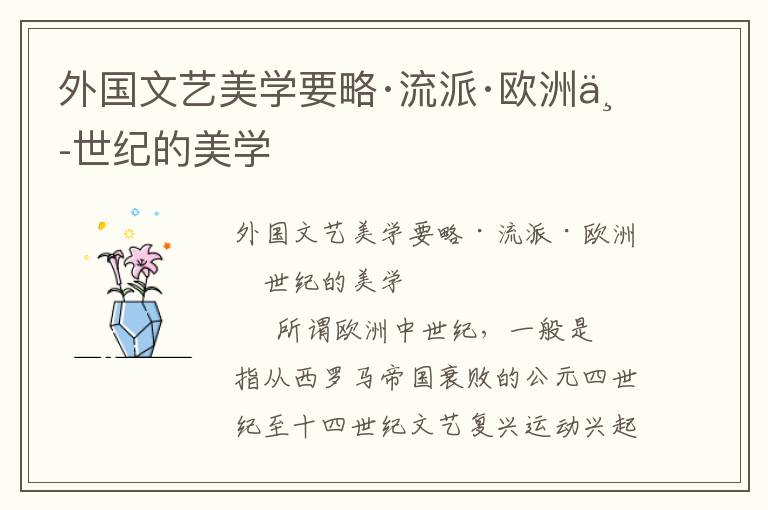
外國文藝美學要略·流派·歐洲中世紀的美學
所謂歐洲中世紀,一般是指從西羅馬帝國衰敗的公元四世紀至十四世紀文藝復興運動興起為止的一千多年的封建社會歷史階段。西方美學從古希臘畢達哥拉斯學派開始,經過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及古羅馬的賀拉斯、朗吉弩斯等一系列美學家承續發展,達到了相當深刻、相當系統的高度。他們的美學思想理論和藝術主張,起到了推動西方文化進步、藝術發展的巨大作用。公元三世紀的普洛丁美學的出現,既標志著古希臘羅馬美學的終結,同時也由此開始了西方美學向中世紀基督教神學美學的歷史轉折。在此后的千年歷史時期中,歐洲的美學和藝術理論幾乎陷于停滯狀態,文藝創作從總體上也宗教化了,直至文藝復興時期,西方美學才得以恢復正常的發展。
在漫長的中世紀,西方經歷了從四世紀到八世紀的“教父哲學”流行時期,從八世紀到十二世紀又有經院哲學的興盛。所謂教父哲學,主要是宣揚上帝的存在,用對基督的信仰取代古希臘羅馬的多神崇拜,鼓吹的是“上帝創世”說、“原罪”說、 “救贖”說,“來世”說和“天啟”說。而經院哲學又是對教父哲學的發展與強化,它將普洛丁的“新柏拉圖主義”加以系統化、神秘化,其核心是主張神權主義、禁欲主義和來世主義.要人們離異“罪惡”的現實世界,通過盲目信仰、禁欲苦修而自救。由于這種宗教神學占據了統治地位,導致當時西方的哲學成了神學的附庸,美學也無法逃脫“神學的婢女”的命運。
從美學理論上看,中世紀時期雖然沒有取消“美”這一概念,但卻把美歸結為僅僅是上帝或神的一種屬性,上帝是一切美的根源,是最高的、永恒的、無限的美。而客觀現實世界的事物美、自然美和藝術美等都是低級的、有限的,其存在的價值,僅在于能使人們通過它們去觀照上帝。其中的藝術美,由于是人的創造,所以是“不真實的或偽造的東西”,是誘發世俗情欲的邪惡的東西,是不能昭示真理的。教會勢力竭力把文藝全盤變作傳播宗教神學的工具。文藝本身作為美學的主要對象的地位也被神學取而代之了。歐洲中世紀美學的基本內容特征,集中地體現在奧古斯丁和托馬斯·阿奎那的神學美學理論中。
奧古斯丁是羅馬帝國基督教教父哲學的代表人物,其美學觀點主要見于《上帝之城》和《懺悔錄》等著作中。他接過普洛丁關于“一切美的源泉在于上帝”的主張,并把美分為有限美與無限美兩種,前者指現實美,后者則指屬于上帝的絕對美,它是高于現實美的“萬美之美”。所謂有限美,只在于“整一”與“和諧”。由于上帝的“整一”性、 “和諧”性本是無限的、不可分的,它是一切作為雜多的、可分的有限美所無法完美地加以顯示的,它們往往妨礙對無限美的認識。據此,他在《懺悔錄》中對文學藝術也備加斥責。他從美是絕對的這一基本思想出發,主張丑卻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它可以納入美的整一體系中,從而把美襯托得更加鮮明。奧古斯丁的美學反映了羅馬帝國衰亡時期的社會思想潮流,為經院哲學美學奠定了基礎。
經院哲學與美學的集大成者托馬斯·阿奎那創建了空前系統的神學思想系統,后被認定為唯一正確的教會哲學。他的美學觀點主要見于《神學大全》一書中。他基本上與奧古斯丁一樣,把美學問題都牽強附會于神學上,盡管他聲稱尊崇亞里士多德,實則是對亞里士多德思想理論中的唯心主義因素大加發揮,以求達到為宗教服務的最終目的。托馬斯的美學觀點,有以下幾個主要方面:
(一) 美在形式。他認為“美有三個因素。第一是一種完整或完美,凡是不完整的東西就是丑的;其次是適當的比例或和諧;第三是鮮明,所以著色鮮明的東西是公認為美的”, “嚴格地說,美屬于形式因的范疇。”因為他把一切可以稱之為美的內容因素,都歸于上帝了,因而必然只從形式上去找美。他所謂的“鮮明”就是“形式上放射光輝”,而它最終只能來自上帝的那種“活的光輝”。在這里,除了陳腐的神學說教和片面套用亞里士多德的美學言論之外,是沒有任何新東西的,
(二) 美具有直觀性與非目的性。在托馬斯看來,由于“美在形式”,所以美自然就是直觀的,即“凡是一眼見到就使人愉快的東西”就叫做美。亦即它僅僅是感官的直接對象,審美不必有理性介入,它與欲念、實用、外在目的等無關,他還明確地說:“美在本質上是不關欲念的”。從中可以聽到康德、克羅齊美學關于美的本質論的先聲。
(三) 美與善的異同。托馬斯一方面主張“美和善是不可分割的”,因為二者都以形式為基礎;另一方面又認為“美與善一致,但是仍有區別”。善是與快感密切相聯的,是欲念的對象,而美與實用目的無關,僅僅是認識的對象,最終通過直觀反應去滿足人的審美需要。
不難看出,在精神實質上,托馬斯·阿奎那的美學觀點與普洛丁、奧古斯丁等人的學說有著明顯的類似與相通,它作為對宗教神學美學的總結,其消極作用是深遠的。這表現在當西方進入帝國主義時期
后,他的理論又被重新張揚,導致有“新托馬斯主義”美學的產生和流行。
歐洲中世紀神學美學,雖然沒有留下更多可供借鑒的思想理論,但對中世紀美學作為西方美學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環節這一歷史地位,還是應予重視的。隨著“中世紀的最后一位詩人”但丁及其帶有人文主義色彩理論的出現,宣告了舊時代的過去,呼喚著文藝復興運動的到來,歐洲又面臨著一個新的美學發展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