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利華《讀畫散記二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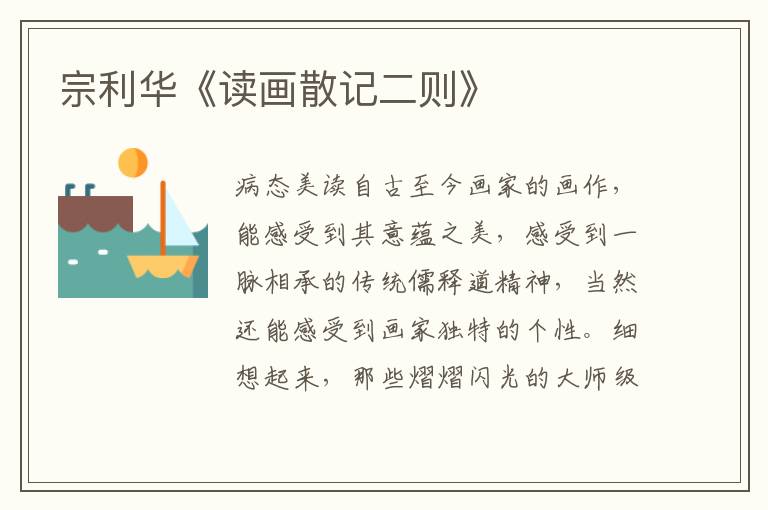
病態(tài)美
讀自古至今畫家的畫作,能感受到其意蘊(yùn)之美,感受到一脈相承的傳統(tǒng)儒釋道精神,當(dāng)然還能感受到畫家獨(dú)特的個(gè)性。細(xì)想起來(lái),那些熠熠閃光的大師級(jí)畫家,或高風(fēng)亮節(jié),或放浪不羈,真是異彩紛呈。探究其性格源頭,我想最早應(yīng)來(lái)自莊子《逍遙游》,他所強(qiáng)調(diào)和推崇的就是絕對(duì)自由,物我兩忘。魏晉時(shí),興儒道互補(bǔ)之風(fēng),士人崇風(fēng)流或風(fēng)度,文人嘯聚山林、撫琴吟詩(shī)作畫成為時(shí)尚,在文人學(xué)者性情演化史上,實(shí)屬濃墨重彩的一筆。隨著佛教禪宗東漸,慢慢浸染進(jìn)去,到宋代又推極簡(jiǎn)之風(fēng),文人畫尤其山水趨于精致,畫家的審美或趣味無(wú)疑更加多元,更顯個(gè)性。到元明清,文人畫已臻完美,達(dá)到高峰狀態(tài),流派紛呈,畫家個(gè)性各異,揚(yáng)州八怪足以證明。
有個(gè)現(xiàn)象,其實(shí)說(shuō)怪也不怪,那就是每逢亂世或朝代更替前,文人學(xué)者、逸士隱士便多,文壇、畫壇更活躍,文藝作品便呈現(xiàn)繁榮。原因很簡(jiǎn)單,每逢此時(shí),政治失控,異族、異兵紛起,戰(zhàn)亂不斷,社會(huì)秩序混亂。為君者、為首領(lǐng)者,多尚武稱霸,多彪悍,因而對(duì)文人(或前朝文人)多排斥與打壓。文人、學(xué)者抗?fàn)巹t手無(wú)縛雞之力,順從則有悖于內(nèi)心。于是參禪論道成為其精神導(dǎo)向,隱居山林成為遠(yuǎn)離漩渦、力求自保的手段。再者,細(xì)數(shù)歷代文人,尤其那些如星月一般者,他們有個(gè)共性,要么在官場(chǎng)上混得一塌糊涂,不斷被貶;要么干脆隱居一隅,君王力邀也不出山,有人即便出了山,卻小心翼翼,嚴(yán)格遵循大隱隱于市之道。文人就這樣一副臭脾氣,不肯妥協(xié),不愿服軟。至于文人畫,便是在此背景下,一路跌宕起伏走來(lái)。當(dāng)然山水一脈尤顯主流。正基于上述原因,文人多流連于山水,肆意或靜修于禪道。王維、董源、巨然、倪云林、沈周、石濤、八大,這些閃耀的巨星,莫不如此。當(dāng)然,于花鳥、人物一派,也是怪才迭出。比如八大,一只鳥、一條魚,即可縱橫天下。再比如梁楷,那個(gè)被稱作“梁瘋子”的,寥寥數(shù)筆,兩幅畫,兩個(gè)和尚,一袒胸露乳,一蹲地朶朶砍竹。畫不在多,就此兩幅,足可笑傲江湖。
不得不說(shuō),文人畫家有幾個(gè)重要特征是比較突出的——癡、癲、狂、迂。
有些人很外在,例子能舉一大把。讀陳傳席先生《中國(guó)山水畫史》,突然發(fā)現(xiàn),“癲狂派”這一流派,居然也是脈絡(luò)清晰。比如,被稱作指畫創(chuàng)始人的唐代張璪,畫畫的時(shí)候,“捽掌如裂”,意思是,用手掌蘸墨在絹素上肆意涂抹,畫完之后,“投筆而起,為之四顧。”那份狂態(tài),自不必說(shuō)。其后的王墨更是“風(fēng)顛酒狂”。作畫時(shí),一高興起來(lái),手腳并用,酷似當(dāng)下的行為藝術(shù)。還有一些,可以稱作因“癡”成“癖”,成了“怪病”。 譬如倪瓚,他的潔癖,簡(jiǎn)直登峰造極!前無(wú)古人,后無(wú)來(lái)者。還有米芾焚香拜石的典故,也是天下皆知,遂有“米癲”之號(hào)。當(dāng)然還有專畫“無(wú)土蘭花”的鄭思肖等。當(dāng)然更多的癲狂是內(nèi)在的,精神層面的。就像八大畫的鳥兒、魚兒的眼睛,白多黑少,活脫脫一副憤世嫉俗、我根本瞧不起你的架勢(shì),這幾乎是自古及今真正文人的共性。仔細(xì)尋究,你會(huì)發(fā)現(xiàn),不管是文學(xué)領(lǐng)域還是書畫領(lǐng)域,文人或畫家對(duì)于這種癲狂的欣賞,也是一致的。因?yàn)椋瑒?chuàng)作嘛,事關(guān)靈魂,高抵生命,必須不拘于心,不囿于俗,所以這叫灑脫,叫脫俗,叫至高境界。非我癲狂,被逼無(wú)奈。外被世俗世道逼,內(nèi)被靈感才情逼,沒辦法,唯有狂,唯有病態(tài)。
但自古至今,真正的高手,真正的藝術(shù)大師,真正創(chuàng)作出傳世佳作的藝術(shù)家,其諸般行徑反倒被視作正常,被當(dāng)作軼事。即便是狎妓出行之類事,也不過(guò)如此,風(fēng)流而已。甚至,后來(lái)的文藝評(píng)論家冠之一個(gè)好聽的名字,叫作“病態(tài)美”。
當(dāng)然,也有不美的例子。對(duì)文人或者畫家的定位,多數(shù)人看法是,須有人品、學(xué)問(wèn)、才情、思想這些基本元素,才算完美。有人把人品列于首,有些人則強(qiáng)調(diào)學(xué)問(wèn)。總之,人品很重要,被人反復(fù)提起。但總有個(gè)別人,作品與人品相去甚遠(yuǎn),甚至嚴(yán)重脫節(jié),與當(dāng)下所說(shuō)的“白天圣人,夜晚禽獸”如出一轍。比較典型的例子是董其昌。論書法繪畫,毫無(wú)疑問(wèn),一代宗師。但生活方面,此人卻實(shí)在讓人不敢恭維。中年之前還勉強(qiáng)說(shuō)得過(guò)去,中年之后,那叫一個(gè)爛,毫無(wú)廉恥。只說(shuō)一件,此人熱衷房中術(shù),渾身燥熱起來(lái)控制不住,路遇佃戶的女兒就強(qiáng)占了去。這事兒都被說(shuō)書的編成小段兒到處唱。有人還把“若要柴米強(qiáng),先殺董其昌”的控訴書貼滿了大街小巷。這哪還有人品之說(shuō)?所以,“病態(tài)美”這頂帽子,無(wú)論如何也戴不到他頭上。
文人畫之所以歷久彌新,與畫家的學(xué)問(wèn)之廣,與其思想內(nèi)涵之高當(dāng)然是緊密相連的。不只是文人畫,所有藝術(shù)門類經(jīng)典留世之作,都是一樣。中國(guó)畫強(qiáng)調(diào)意蘊(yùn)和氣息,正是如此,觀畫之時(shí),你說(shuō)不出來(lái)卻真正打動(dòng)你的那些東西,就是這個(gè)。真正具有標(biāo)簽性的,具有強(qiáng)烈識(shí)辨性和專屬性的,是學(xué)問(wèn)和思想。學(xué)問(wèn)深,思想精,決定了作品經(jīng)典。既如此,病態(tài)一下又何妨?
我心在野
在野派畫家,自古有之,然而命名在野,我想歷史還沒多么久。因?yàn)樽怨胖两瘢嫾业脑谝芭c不在野,實(shí)在沒一個(gè)涇渭分明的界限劃分。大范圍說(shuō),只是與學(xué)院派有所區(qū)別而已。當(dāng)然細(xì)分析起來(lái),其風(fēng)格更具獨(dú)特氣質(zhì)、獨(dú)特情懷。而且,在野派與文人畫派交融應(yīng)該更為緊密一些。因歷代文人畫家,在野者數(shù)不勝數(shù)。隨手舉例,倪瓚、沈周、四僧、八怪,都屬此列。
我是更喜歡在野派畫家畫作的。
首先凡歷史上在野的文人學(xué)者,能自開一派、蔚為大觀、流芳百世的,在精神層面上,都算得上是特立獨(dú)行的人。這是很關(guān)鍵的。人貴在精神自由,所謂活得灑脫,活個(gè)痛快,當(dāng)然也“難得糊涂”。不為強(qiáng)者而折腰,不為世俗而羈絆。狂風(fēng)驟雨亦逍遙,明月清風(fēng)來(lái)做伴。這人生,是何等精彩啊!能抵達(dá)此境界者,實(shí)在匱乏。另者,其人品、才情、思想與作品的對(duì)等關(guān)系,是一眼可辨的。看畫久了,一打眼,畫面上便出現(xiàn)其作者形象。那些痕跡烙印明顯的自是不必說(shuō)。看著寂寥的幾棵樹、一架茅亭,自然就想起倪云林來(lái)。看著只用墨色形成的魚、鳥、鹿,當(dāng)即就想到“似笑似哭”的八大。而且這些作品,是能從中強(qiáng)烈而分明地感受到其畫外音的。換個(gè)現(xiàn)代說(shuō)法,是具有原創(chuàng)色彩、獨(dú)立人格的。
現(xiàn)代的在野派畫家,公認(rèn)的有四大家,陳子莊、黃秋園、陶博吾、張朋。這真得感謝陳傳席先生,因?yàn)檫@一說(shuō),是他在《現(xiàn)代中國(guó)畫史》里正式提出的。另外,尚有徐生翁、熊靜安等近年來(lái)也多被提及。
這些人,之所以被冠以在野之名,是因?yàn)樗麄冋嬲疵白愿是寮拧保嬲按箅[隱于市”。他們或生前籍籍無(wú)名,或直到晚年方為人所知。黃秋園是銀行職員,陳子莊是文史館員,陶博吾與張朋則大半輩子都在教學(xué),陶博吾教的還是女子中學(xué)。陳子莊相對(duì)復(fù)雜些,他這一生,算是一部傳奇大書。早年習(xí)武,喜交豪杰,后對(duì)書畫感興趣,曾結(jié)識(shí)黃賓虹、齊白石,但真正的壯舉,是他搭救了張瀾。因此也惹惱了蔣介石,卷入政治漩渦,直至后來(lái)做了文史研究館館員,急流勇退,心想寂寞,遂成一代大家。黃秋園是典型的大隱。老先生生前都沒辦過(guò)畫展。死后兒子為給其做畫展,據(jù)說(shuō)還送出他好多畫去鋪路搭橋。然畫展一開,引來(lái)李可染先生仰天一嘆:“國(guó)有顏回而不知,深以為恥。”這一句話,實(shí)在是比一大摞書畫評(píng)論還要有力度。“秋園皴”至此浮出水面,轟動(dòng)畫壇。也算帶有嘲諷意味地印證了那句話——“是金子總有發(fā)光的時(shí)候。”至于張朋和陶博吾,區(qū)別在于張朋幾乎是完全自學(xué)成才,陶博吾還算得上是科班。因后者讀過(guò)美術(shù)學(xué)校,師從過(guò)黃賓虹、潘天壽等人。究其四人,生活場(chǎng)景,大多偏居一隅——一位四川,兩位江西,一位山東,皆遠(yuǎn)離中心,加上自己靜守一方,自取寂寞之道,因此這在野,也就野得很到位。
當(dāng)然,我真心想說(shuō)的野的重心,還是其作品之野。
說(shuō)到對(duì)畫的喜歡,實(shí)在是個(gè)人喜好。同一幅畫,褒貶不一,也是有的。所有人皆叫好,倒是比較可疑。更不必說(shuō)如黃賓虹者,其黑山水一出,一片倒戈聲。因此,也惹出老先生一句“讖語(yǔ)”:“五十年后方有人懂。”五十年后,果然,一邊倒的好評(píng)。我個(gè)人比較喜歡的書法家,一是米芾,一是蘇子瞻,因此,又喜歡王鐸。想來(lái),這屬于硬朗灑脫一派。至于二王,臨一陣子,不得其法,就感覺擰巴起來(lái)。至于畫,山水一派,尤喜黃公望、倪瓚、沈周、石濤,至近的黃賓虹等,花鳥當(dāng)然是徐渭、八大,近則有齊白石等。盡管讀畫史不深,歷代各家的來(lái)路還不是那么清楚,但對(duì)口味之畫,一觀可知。
此四位在野先生,我最喜歡黃秋園和陳子莊。其作品一繁一簡(jiǎn),一山水一花鳥,各有異趣,自成一家。黃秋園的山水初觀密不透風(fēng),“上不留天,下不留地”,細(xì)細(xì)瞧則山石樹木宛然,古意清意逼迫而來(lái)。尤其他晚期所作山水,層巒疊加,錯(cuò)落有致。老木扭曲遒勁,宛如老僧。此細(xì)密畫法,原本覺得不如簡(jiǎn)的有趣,后來(lái)漸漸也喜歡進(jìn)去。畫壇有大畫、小品之說(shuō),各領(lǐng)風(fēng)騷而已。至于技法上,密不透風(fēng)和疏可走馬,都是至難。觀一幅大畫,好比讀一部長(zhǎng)篇,起承轉(zhuǎn)合,龍骨蜿蜒所在,乃至曲徑通幽,雜花生樹,就顯出其大氣磅礴來(lái)。至于小品,尺幅雖小,畫材雖簡(jiǎn),但四兩撥千斤。陳子莊的畫,就屬此類。齊白石先生說(shuō):“似者媚俗,不似者欺世,妙在似與不似之間。”一語(yǔ)概括了陳子莊。記得我那時(shí)正細(xì)細(xì)研讀朱新建的線條及色彩,偶遇陳子莊,立刻被他吸引。其畫面結(jié)構(gòu)奇特,下筆用墨曠達(dá),看似不經(jīng)意揮灑,實(shí)則內(nèi)在韻律十足,天然異趣。不管黃秋園的繁,還是陳子莊的簡(jiǎn),都個(gè)性十足,均不可復(fù)制。畫家抵達(dá)這一境界,實(shí)屬至佳。從古至今,學(xué)大師之作當(dāng)小心,不管書法還是繪畫,都有“打進(jìn)去,跳出來(lái)”之說(shuō),打進(jìn)去不容易,跳出來(lái)則更難。“學(xué)我者生,似我者死”,就是這理兒。
相比較而言,現(xiàn)代這幾位在野派畫家的題畫詩(shī)或自作詩(shī)里面,我還是喜歡陶博吾和熊靜安,此二公文采斐然,書法也妙。比如,陶博吾曾有詩(shī)云:“他鄉(xiāng)除夕無(wú)陳設(shè),借得鄰家兩個(gè)瓶。折取梅花伴翠柏,也叫春色滿寒庭。”這就是典型的在野心態(tài)了。當(dāng)然,熊靜安所詩(shī):“自稱天涯一楚狂,秋蘭為佩籬為裳,怒將白眼觀今世,笑把丹心燃夕陽(yáng)。”亦如出一轍,只不過(guò)稍稍狂了一點(diǎn)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