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美學基本理論·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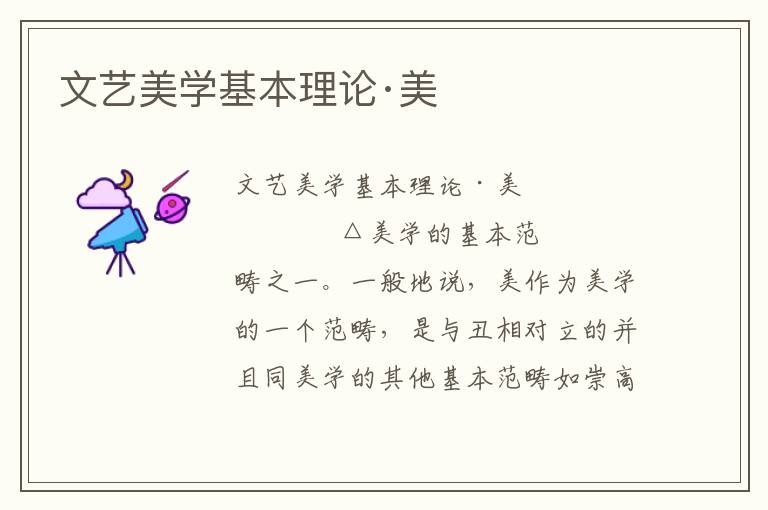
文藝美學基本理論·美
△美學的基本范疇之一。一般地說,美作為美學的一個范疇,是與丑相對立的并且同美學的其他基本范疇如崇高、滑稽、悲劇、喜劇等等也有所不同。作為美學范疇的美,是與上述諸范疇共同表征的具有普遍意義的美相區別的狹義的美。從根本上來說,對包括美在內的美學范疇的界定、描述和探究,同對美的根源、美的本質的哲學理解是緊密相關的。
按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點,美離不開人,離不開人類實踐,離不開人類社會生活。確切地說,美是在“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為基本表現形式的實踐中形成的。因此,美的本質與人的本質是緊密相關的。我們只有在上面粗略描述的途程中,思索、探尋,才能或許對美是什么這個千古之謎,作出較為符合歷史實際的回答。從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點來說,作為美學范疇的美,其中見不到人類艱苦實踐的過程以及這一過程留下的印痕。它是完善、充實的自然人化,也是人的本質力量如認知、情感、意志等等充分、完整的體現,是主觀與客觀、感性與理性、現實與理想、本質與現象的統一。要而言之,美是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的完美結合并通過和諧宜人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完美現象形態。從感性的外在形態來看,美很象范仲淹筆下的春光明媚中的湖光山色:“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傾;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從以上可以看到,這里是客觀規律即真為主體所把握,人的主觀目的即善成為對象化的善,是真與善的真正統一。
美是人類社會實踐(主要是生產勞動實踐)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在“人猿相揖別”的初民時代,美是無從談起的。這個時期的自然界,以其粗獷獰厲的形態和神秘莫測的內蘊,成為人類的敵對力量。用馬克思的話說,這時的自然力, “是某種異己的、神秘的、超越一切的東西”,而這時的社會力量“和自然力量本身一樣,對人來說是異己的,最初也是不能解釋的,它以同樣的表面上的自然必然性支配著人”。只有在外在的自然的人化的程度、人的內在本質豐富的程度,都達到一定的歷史水平的時候,人們才會從圖騰崇拜、宗教巫術的被動感受中振奮起來,驚醒起來,去領略萬紫千紅的美的世界。這樣的結果,是作為實踐主體的人類經過艱苦卓絕的長期斗爭才獲得的。
同其他美學范疇一樣,美既有內容,又有形式。它們之間的關系,是辯證統一的關系。也就是說,美的內容與美的形式之間的這種辯證統一關系,既不象崇高那樣突出嚴峻而沉重的形式,也不象滑稽那樣突出渺小而輕佻的內容。美是和諧的。這種和諧體現在內容和形式的關系上,前者偏重嬌弱、柔順、平易,后者則突出比例、對稱、均衡,美是上述兩者恰到好處的渾然一體的融合。十八世紀英國美學家博克曾經描述過這種和諧的美:第一 ,比較小;其次,光滑;第三,各部分見出變化;但是第四,這些部分不露棱角,彼此象熔成一片;第五,身材嬌弱,不是突出地現出孔武有力的樣子;第六,顏色鮮明,但不強烈刺眼;第七,如果有刺眼的顏色,也要配上其他顏色,使它在變化中得到沖淡。博克的上述概括,盡管帶有明顯的經驗觀察性質,但也約略地指明美這一范疇的和諧的特點。進入審美活動之后,由于美呈現不同的形態,審美主體對于美的內容和形式及它們之間的具體感受也有一定的區別。社會美以內容勝,其中強調的是實現了的社會審美理想,即偏重于倫理意義的善; 自然美則以形式勝,強調的是于形式把握中的無所為而為的欣賞把玩。藝術中的美,是藝術家根據客觀現實生活材料并滲入主體情思的加工制作,在主觀上就有把內容與形式完美地結合在一起的愿望,所以它是情與理、形與神、感性與理性、內容與形式的統一。
在審美主體的美感經驗中,美所激起的,是情感上寧靜和諧和感知上的賞心悅目。它不象主體面對崇高的現象形態那樣,所激起的是先逆后迎、微帶痛感的亢奮情緒狀態;也不象欣賞悲劇那樣,是摻雜著恐懼和憐憫的道德力量的感召。車爾尼雪夫斯基說: “美的事物在人心中所喚起的感覺,是類似我們當著親愛的人面前時洋溢于我們心中的那種愉悅。”朱光潛也說,面對審美主體, “它是不會反抗的,似乎總是表現愛與歡樂,喚起我們的愛慕”。總之,在欣賞美的經驗中,所形成的美感是主體通過“欣賞音樂美的耳朵”和“感受形式美的眼睛”直接加以捕捉的美感,是伴隨著賞心悅目的快感的美感。
(洪鳳桐)
△美學的基本范疇之一。一般地說,美作為美學的一個范疇,是與丑相對立的并且同美學的其他范疇如崇高、滑稽、悲劇、喜劇等等也有所不同。作為美學范疇的美,是與上述諸范疇共同表征的具有普遍意義的美相區別的狹義的美。從根本上來說,對包括美在內的美學范疇的界定、描述和探究,同對美的根源、美的本質的哲學理解是緊密相關的。因此,由于在有關美的根源、美的本質問題上的哲學理解不同,所以歷史上各派美學對美這一美學范疇的界定、認識和描述也有所不同。
朱光潛對美這一范疇所作的界定、描述和探究,是同他在有關美的根源、美的本質問題上的哲學探討聯系在一起的。早在三十年代,朱光潛認為,美不僅在物,亦不僅在心, “它在心與物的關系上面;但這種關系并不如康德和一般人所想象的,在物為刺激,在心為感受;它是心借物的形象來表現情趣”。他又說: “世間并沒有天生自在、俯拾即是的美,凡是美都要經過心靈的創造。”這里,朱光潛雖然沒有把美作為一個范疇來探討,但我們可以從中看到朱光潛有關美這一范疇的基本見解。在他看來,美同其他美學范疇一樣,存在形式是形象,或者毋寧說是經過心靈創造的表現情趣的形象,亦即藝術形象。用朱光潛的話說, “美就是情趣意象化或意象情趣化時心中所覺到的‘恰好’的快感。”
朱光潛在《悲劇心理學》一書中,當談到悲劇感的時候,曾論及“秀美”在情感上的效果;秀美的東西往往是嬌小、柔弱、溫順的,總有一點女性的因素在其中。它是不會反抗的,似乎總是表現愛與歡樂,喚起我們的愛憐。我們對于秀美的事物的反應,也似乎總是取一種保護者、或至少是朋友的態度。朱光潛所談的秀美,雖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作為美學范疇的美,但兩者在品質上卻是接近的。
建國后,朱光潛根據自己理解的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點,認為“美是主觀與客觀的統一”。他指出,美是形象,美是客觀方面某些事物、性質和形狀適合主觀方面意識形態,可以交融在一起而成為一個完整形象的那種特質。總起來看,美是形象,是意識形態性的形象;主客觀統一過程,就是藝術活動過程,而藝術活動過程就是生產勞動過程。
無論是建國前還是建國后,朱光潛的下述觀點是一以貫之的,即:物本身的美只是自然形態的美,不是美學意義的美,它只具備美的條件;只有物的形象即藝術形象才具備美學意義的美。這就是說,舉凡美的現象形態都是普泛的藝術形象。通常所說的自然美這個概念有兩種含義。一種是指自然物本身的美,但它只是自然形態的美,還不是美學意義的美;一種是指自然物的形象,這是“一種雛形的起始階段的藝術美”,后一種自然美才是美學意義的美。朱光潛指出: “丑與美不但可以互轉,而且可以由反襯而使美者愈美,丑者愈丑。”朱光潛拿自然中的美丑與藝術中的美丑作了比較分析。他首先說,自然中的美丑,同藝術中的美丑不是一回事。自然中的美丑在它的自然形態的美丑的意義上,都不是美感經驗以內的價值,即都不是美學意義上的美丑。藝術中的美丑則與此恰恰相反。它是美學意義上的美丑。其次,朱光潛指出,自然美或自然丑是可以轉化為藝術美的。他說: “本來是一個很丑的葫蘆,經過大畫家點鐵成金的手腕,往往可以成為杰作。大醉大飽之后睡在床上放屁的鄉下老太婆未必有什么風韻,但是我們誰不高興看醉臥怡紅院的劉老老?從前藝術家大半都怕用丑材料,近來藝術家才知道熔自然丑于藝術美,可以使美者更見其美。”這就說明,藝術必根據自然,但藝術美并不等于自然美,而自然丑也可以轉化為藝術美。再次,朱光潛認為,自然美也可以轉化為藝術丑。長在藤子上的葫蘆本來很好看,如果你的手藝不高明,畫在紙上的葫蘆就不很雅觀。許多香煙牌和月份牌上面的美人畫就是如此,以人而論,面孔倒還端正,眉目倒還清透;以畫而論,則往往惡劣不堪。
(洪鳳桐 編述)
△美是一種客觀存在,并且是美學科學的主要研究對象和最重要的范疇之一。在客觀世界中本來就存在著美。人類很早便開始了對美的認識。在我國殷墟發現的甲骨文中,已經有了“美”字。西方在古代希臘,也有了對美的種種探討。在人類對美的探討中, “美在哪里”的問題是首先要回答的問題,也是美學的最基本的問題。在漫長的美學思想史上,對這個問題的回答眾說紛紜,爭訟不休。但根本說來,人們的回答總與他們對哲學基本問題的回答是一致的。概括地說,主觀唯心主義美學總是在人的主觀感覺和意識中去尋找美,客觀唯心主義美學總是把神或理念當作美的本體或本原,只有唯物主義美學堅持從現實事物去考察美,認為美就存在于客觀現實之中。在這里,只有唯物主義美學的回答,才是唯一正確的回答。
客觀的美是豐富而多樣的。根據美的產生條件的不同和性質的不同,可以把美分為現實美和藝術美兩大類別。現實美是指現實事物的美。現實美又包括自然美和社會美,也即自然事物的美和社會事物的美。與現實美相對待的藝術美,則是藝術家按照美的規律而能動地創造的美,它存在于各種具體的藝術作品之中。自然美和社會美,現實美和藝術美,它們既互相區別而不容混淆,又互相聯系而不能割裂。人類對美的探討,還有另一個重要問題,這就是“美是什么”,也即美的本質問題。人類對這個問題的認識,經歷了一個從不知到知、逐漸深化的過程。最初,人們往往把事物的美混同于事物的實用性, “美”與“善”、與“好”常常混用不分。這種混亂甚至一直存在于后來的美學思想中。從這個意義上說,德國古典美學將真、善、美三分而并列,對美的特性的認識是一種歷史性進步。但是另一方面,真、善、美雖不能等同,卻又有聯系,并不能截然分開。具體說,自然美是與自然的真一致的。真的事物未必都是美的事物,但美的自然事物一定體現著自然的必然,一定是真實的實際事物。社會美則與社會的善是一致的。美的事物未必都是善的,但善的事物一般地說就是美的社會事物,美的社會事物一定都是善的。
人們又曾把事物的美歸結為事物的形式,認為事物的對稱、均衡、和諧等形式決定著美之所以為美。當然,在自然美中有美的自然現象; 自然現象的美,與一般理解的形式有密切的關系,甚至在一定意義上說就是由它們決定的。但自然現象美體現著自然的必然,不宜簡單地視為形式的美。除此之外,其他事物的美都與形式有一定的關系,但是,這些事物之所以美,卻不是由它們的形式決定的,而根本是由它們的內容決定的。當然,形式本身也有美不美的問題,相對獨立的形式美及其規律確實是存在的,形式美對事物的美有積極的影響。不過,把美的本質歸結為形式,顯然是錯誤的。
從根本說來,美是一種規律,是美的事物和現象之所以美的規律。美的規律看不見、摸不著,卻真實而客觀地存在于一切美的事物和現象之中,決定著它們的性質、
發展過程和必然趨勢。這個規律就是典型的規律。所謂典型的規律,是指非常突出的現象充分地表現出事物的本質,非常鮮明、生動的個別性有力地表現出事物的普遍性。典型的規律既是藝術美的規律,也是自然事物的美的規律、社會事物的美的規律。事物的本質或普遍性,總是要表現在它的現象上,不表現是不可能的;但表現得不充分、不突出,便不可能是美的。因此,美的事物就是典型的事物,事物的美之所以美的本質就在于事物的典型性。事物的典型性決定著一事物成為美的,事物的典型性的發展變化決定著該事物的美的發展變化。正因為如此,所以又可以說,美就是關于客觀事物的具體形態的本質真理。當然, 自然美、社會美和藝術美在美的規律上還各自有它們獨特的規定性。現在,這些方面美的規律的獨特規定性正在得到深入的探討,已經獲得了可喜的成績。
(嚴昭柱)
△美學的基本范疇之一。歷史上各派美學對美的根源、美的本質的哲學理解不同,對美這一范疇的界定、認識、描述也有所不同。李澤厚認為,要搞清什么是美,首先應該吸收分析哲學的積極成果,把概念搞清楚。李澤厚對“美”一詞做了如下的語義分析。一、根據對“美”的字源學的兩種解釋(一說羊大為美,另一說羊人為美),認為美與感性存在,與滿足人的感性需要和物質享受(好吃)有直接聯系;美還與原始巫術禮儀活動有關,具有某種社會性含義,并且和人的群體意識和理性緊密相連。二、根據“美”在日常語言中的三種相互聯系又相互區別的含意,美是(1)表示感官愉快的強形式,(2)倫理判斷的弱形式, (3)專門指審美對象。只有第三種意義上的美才是美學范疇的美,才是審美判斷。
李澤厚又對美學范圍的美做了結構上的分析,認為它有幾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審美對象。西方美學家大多把審美對象看成美,而審美對象是由人們的審美感受、審美態度創造出來的。作為客體的審美對象也確實是依賴于主體的作用才成為對象的,沒有審美態度,再美的藝術、風景也不能給人以審美愉快,不成其為審美對象。美作為審美對象離不開人的主觀意識狀況。第二層含義是指審美性質。一個事物能否成為審美對象光有主體條件不行,還需要對象上的某種東西,即審美性質。無論人的主觀條件起多大作用,總還是有一定的客觀根據,和一定審美性質相關,最終仍不能脫離客體一定的審美性質。審美性質確有一定客觀形式規律,這是不能忽視的。特別在造型藝術中,所謂按美的規律來造形也包含了這一層的含義。但這些形式規律是如何來的?為什么一定的比例、對稱、和諧、多樣性統一、黃金分割等等會成為美呢?這個相當棘手的問題是客觀派美學一直解釋不清的。第三層含義則是美的本質、美的根源。我們探求美就是要用馬克思主義哲學觀點找出美的普遍必然性的本質、根源。由于人類的社會實踐,才使得某些東西具有審美性質,最終成為審美對象。因此,社會實踐是美產生的根源,規定美的本質。如果把審美對象當作美而加以論證,就產生各派主觀論(美感決定美)的美學理論;如果把審美性質當作美而加以論證,則產生各派客觀論的美學理論。
李澤厚特別強調要注意“美”這個詞是在哪層含義上使用的。注意你所謂的“美”到底是指一個具體的審美對象,還是指對象的審美性質,或是指美的本質和根源。我們爭論美是主觀的還是客觀的,只能在第三層意義上進行。因為所謂美是主觀的還是客觀的,并不是指某個具體審美對象,也不是指一般的審美性質,而是進行哲學探索,即研究“美”從根本上到底于如何來的。是心靈創造的?上帝給予的?生理發生的?還是別有來源?所以它研究的是美的根源、本質,不是美的現象、審美對象或審美性質等。從審美對象到美的本質,這里有問題的不同層次,不能混為一談。
李澤厚認為,美具有兩個重要特征,即客觀社會性和具體形象性。所謂美的客觀社會性是說美不屬于社會意識范疇,而屬于社會存在范疇。美的客觀社會性是美的基本特征,是由實踐的客觀社會性決定的。所謂美的具體形象性,即美必須是一個具體的、有限的生活形象的存在。形象就是事物的樣子、形式。美的真與善統一的內容必須通過形式表現出來,美的形式是自由的形式。
李澤厚認為,美的本質是真與善、規律性與目的性的交融統一。美的形式是自由形式。因而“真善的統一表現為客體自然的感性自由形式是美”。








